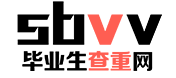摘要:在文学文化研究领域中探索异国形象的建构,即是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研究的传统课题,又是跨文化跨学科的综合性课题发展的内容,该项课题的跨学科性和边缘性,就为其从不同的文化领域进行文学文化研究提供可能,因而具有突出的比较文学的研究特点。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通过中国情人形象的建构,在东西方文化中,寻求自己的文化之根。笔者从小说《情人》入手,浅析杜拉斯复杂矛盾的文化归属、在“他者”形象塑造中的“自我”内化、多重文化的关联及作者的异域情怀。
关键词:异国形象;情人文化;归属他者;自我

作为比较文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形象学近几年在理论和方法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从形象研究入手,能够对人们表面观察到的东西,发掘出更为有价值的深层内涵,为深入认识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社会心理提供更多的参考资料。狄泽林克《关于“形象”与“幻想”及其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法国学者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形象》及保尔•利科《在话语和行动中的想象》等形象学研究纲领性文论所建构的形象学理论,对西方形象学理论的进一步阐释与拓展为我国形象学研究者们指明了方向,也成为他们研究西方“中国形象”的利器。
在文学创作中受到一定的文化氛围影响,渗透一定的时代、地域、民族文化气息,形成区别于他者的文学风格。换言之,作家所生活的时代、地域都会对作家的创作埋下潜在的文化内涵。玛格丽特•杜拉斯创作中多元化的文化内蕴,就拜赐于少年时期越南的殖民记忆、非议情感世界中的中国情人和隶属法国国籍的文化认知。东西异国文化在她身上交流、碰撞,使其创作具有丰富而多变的文化内涵,成就了这位享誉世界的多面手作家。杜拉斯于1984年创作的小说《情人》是一本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并凭此获法国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从此,伴随其一生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中国情人形象陆续出现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等几部作品当中,几乎从未停止叙写“我”与异国情人的故事,从未放弃塑造堪称20世纪法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形象之一的“中国情人”。本文将从作者复杂的文化归属、他者形象建构中的自我内化及异域文化创作中的精神投射三个方面,并结合杜拉斯生平事迹的记述,对杜拉斯《情人》进行深入理解,浅释其创作的精神内涵。
一、作者复杂矛盾的文化归属
(一)越南生活在创作中的记忆
1914年4月四日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在法国殖民地越南西贡附近的白人居住区,她的童年、少年都是在印度支那度过的,十八岁才返回祖籍法国。童年的生活环境和经历在潜意识中形成其独特的文化之韵,为其创作提供不竭源泉。在劳拉•阿莱德尔所著的《杜拉斯传》中写到的那样,“印度支那殖民地,这已经成了她的生命的底片”①。在杜拉斯的世界里越南的记忆历历在目:
“渡船四周的河水齐着船沿,汹涌地向前流去,……水流所至,不论遇到什么都被卷去。不论遇到什么,都让它冲走了,茅屋,丛林,熄灭的火烧余烬,……都被大水裹挟而去,冲向太平洋,连流动的时间也没有,一切都被深不可测、令人昏眩的旋转激流卷走了”②(20)。
在杜拉斯看来,力量、激情、狂野使湄公河充满魅力,每每相遇都如同新鲜的血液冲击心底,掀起生命的狂澜。这沃土上疾驰的河流,犹如杜拉斯狂奔的自由思想,在这东方的异域国度寻求灵魂的归属。
“有焦糖的气味侵入,还有炒花生的香味,中国菜汤的气味,烤肉的香味,各种绿草的气息,茉莉的芳香,飞尘的气息,乳香的气味,烧炭发出的气味,……城市的气味就是丛莽、森林中偏僻村庄发出的气息。”③(36)
可嗅之味,可见之色,可闻之声,引我们亲临神秘的热带丛林,重访旧时的越南殖民异域。
童年特殊的成长经历,流淌在儿时记忆中的点滴美丽,紧紧地将杜拉斯拥进东方文化、异域魅力的怀抱,连接着终其一生也无法割断的文化之源。
(二)法国文化的优越感体现
18岁杜拉斯回到祖国故土,面对法国文化的缺失,她并非没有尝试融入法国文化,也曾将法兰西作为生活的背景抒写自己内在的情感,接连创作了《平静的生活》《无耻之徒》,但都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失败闹剧告终。自此,杜拉斯重新审视自己的艺术构思,《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是创作中对东方异域文化的第一次较成功的展示,1984年《情人》的出版,获得了当年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是杜拉斯深刻的认识到东方文明、异域情调、对其创作的个性品质形成的影响。在彬彬有礼的法兰西国度,根本容不下她狂放不羁的自由思想,将归属感与法国远远地割离开来。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居所》的谈话录中,说得更加明白:“她没有时间照看我们,再也不去想她的孩子们,因此,我们就到处乱跑,不是整日呆在树林中,而是在小河边、在湍流的小溪边流连忘返,我们所称为的小溪就是那些奔向大海的湍流。我们打猎。那里的童年与我们这里的完全不同,你瞧,我们与其说是法国人不如说是越南人。现在我才发现了这一点,我们法国血统的外表,法国籍的这种外表完全是虚伪的。我们跟那些越南小孩一样说越南语,跟他们一样不穿鞋,……”在杜拉斯看来,她已将越南所属的东方文化作为其生命的起点和文化的根源。
(三)两者文化冲突造就的中国情人
但这并不意味杜拉斯摆脱了东西方文化之争,相反,特殊的身份,使她面对西方文明常处于无根的状态,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杜拉斯既不从属东方文化,又无法融入西方文明,终其一生徘徊于过去和现在之间,游离于“文明”和“野蛮”之中。在其作品中不难看出她所寄托的矛盾和尴尬。在《情人》中,随处可见“我”作为法籍白人在越南殖民领地所能感受到的种族优越感。“我”和家人是住在白人专属地域,客车上有预留的白人专属座位,在面对中国情人宴请时可以心安理得接受一切,没有道谢,连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我”与中国情人的关系,将作者处于东西文化夹缝中的两难处境表现的淋漓尽致。当“我”踏上返回法国的轮船:“当轮船发出它第一声再见的长鸣,……她哭了,但没有让泪水流出来。他是个中国人,不该为这样一个情人哭泣。她没让妈妈和小哥看出她很痛苦,什么也没让他们看出来。……她知道他在看着她。她也在看他。她看不到他了……码头变模糊了,大地也渐渐消失了。”④(96)
这不仅仅是“我”与异域情人的别离,更是对东方文化的一次分离。越南的童年记忆和法国的文化国籍,使杜拉斯一生背负文学创作的双重文化内涵。
二、“他者”形象建构中的“自我”内化
在当时的印度支那,种族歧视、等级观念可谓根深蒂固。在等级森严的殖民地社会,杜拉斯一家是处于最底层的白人家庭,因贫困在法籍白人中受尽排斥和鄙夷;贫穷的命运使他们的生活更为接近当地的殖民地居民,但作为白人,他们仍优越于当地土著人,这使杜拉斯面对东方文化的时候,在潜意识中认同了白人的身份地位。在对白人身份认同的同时,使得她将俯视的目光投向第三世界的人们,在有意或无意的文学创作中赋予他们“他者”的形象特质。《情人》中的中国男人身上充斥着东西文明的交融和矛盾,这种“他者”形象的建构将杜拉斯的文化之根深深植入她的创作。
异国形象是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对另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也就是说在比较文学中,形象学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构建和叙述,对他者形象的认知是其创建的基础。在杜拉斯《情人》中对中国情人的塑造,不仅是杜拉斯个人经历的投射,更是代表法兰西文化对第三世界的认知。
(一)杜拉斯“他者”形象建构和“自我内化”
杜拉斯并没有来过中国,她对中国的感知显然并不是自己的接触,而是受到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社会集体想象的影响。在《情人》中,杜拉斯选取十五岁的白人姑娘独自站在渡口为场景,让这位二十五六岁的中国青年与其在湄公河第一次相遇。面对未成年的女孩,他显得手足无措,即便在拥有绝对的经济优势、留学别国的见识,他的手仍然发抖。同样站在都拉斯的角度她也足以使其胆怯,因为他是中国人,黄种人,在等级森严、阶级层次分明的时代,种族差别,肤色优劣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在整个情感经历的过程中,白人小姑娘一直处于主动地地位,第一次邀约,第一次去堤岸的单身公寓,都是“我”在主宰情感的命运。相反,中国男人始终处于一种被动、从属的地位,以至于通篇都未出现他的名字,他是软弱的、没有主动性的,依附于家庭,无法摆脱家庭的挟制,无法战胜恐惧去争取爱,没有勇气去承担爱情的责任。这种羸弱的形象创造正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集体想象,蔑视的情绪显而易见。
巴柔说:“所有对自身身份依据进行思考的文学,甚至通过虚构作品来思考的文学,都传播了一个或多个他者的形象,以便进行自我结构和自我言说:对他者的思辨就变成了自我思辨”。⑤(179)从精神分析理论出发,“他者”形象的构建是对与自我相对方向的确认,创造形象秩序,从而确立自我意识,确定主体所缺失的或主题所寻找的内在“自我”。尽管在整部作品中中国情人的形象并没有得到逆袭式的转变,但在文章开篇作者有这样一段描述:
“我已经上了年纪,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他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对我说:“我始终认识您。大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诉您,依我看来,您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漂亮,您从前那张少女的面孔远不如今天这副被毁坏的容颜更使我喜欢。”⑥(1)
与其说开篇情景是自我自恋式的幻想,不如仔细想想用此开篇,统领整部著作的实质。笔者看来,《情人》本身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作者开篇对一个久别男子对“我”倾慕,实则是作者内心创造的与中国情人再次重逢的场景,而此男子已在“我”记忆中已没有了特别的纪实,这样的描述符合白人“我”在面对东方殖民属地时的高傲情绪,奠定在整部作品中的“情人”的从属地位。
那在这段异国恋情当中,“我”对待中国情人到底是怎样一种情感呢?
在文章结尾作者又有这样一段叙写:
“战后多少个岁月过去了,从前的那个白人姑娘几经结婚、生育、结婚、写书。一天,那位昔日的中国情人带着妻子来到巴黎。他给她挂了个电话。是我。一听到这声音,她便立刻认出他来。他说: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说:是我,你好。他有点胆怯,他和从前一样感到害怕。他的声音突然颤动起来,而这一颤动,使她突然发现他那中国的口音。”⑦(95)
事实上,中国情人依旧没有摆脱对白人女子的胆怯,而“我”对这段感情也一样未曾忘怀,深切的记得那并不特别的声音。
在杜拉斯的异国想象建构中,中国情人是一个虚构的“他者”镜像,承担的是杜拉斯的东方文化之根,在东西方文化冲突和矛盾之中,白人永远是作品的主宰,在西方的俯视下,异国情人始终扮演着陪衬的配角,在这凄美的“异域爱情”故事的帷幔下,杜拉斯的文本中有意或无意的隐藏着她所认同的种族的排序。
(二)法兰西文化在“他者”形象创建中的投射
异国形象的塑造对建构者杜拉斯所从属的法国文化来说,也具有某种特定的表达,《情人》里中国情人的构建,投射出法兰西文化的剪影。
首先是对物质欲望的占有。杜拉斯的父母和很多居住越南的白人殖民者一样,怀揣着寻金的梦想来到殖民地。在《情人》中,“我”的母亲在堤岸附近买了一块地,经常被海水淹没,从此发财梦幻灭;“我”与中国情人的相遇,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黑色的轿车,车里有折叠式的坐席,接着才发现大轿车里的男人在看她;爱情开始不久,“我”的手上便有了价值不菲的钻戒等等一系列情景的创设,这种对物质占有的欲望,对金钱财富梦寐以求的想象,实质上是法国对印度殖民地物质掠夺缩影,简写出物欲横流中对财富的谄媚。
其次,“我”与中国情人在文化间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情人身上有一种优雅、温柔、循规蹈矩,东方男人身上有着传统女性之美,也是东方人儒雅之风的传承;而年仅15岁的白人女孩沿袭了西方奔放的情怀,热情、开放、自由充斥着整个生命。二者文化的差异、双方互补的性格,才使这段感情的萌发提供了可能,使他们都深深爱上彼此,同时也注定了这段感情有始无终。
在异域情人的创设中,既反映出作者矛盾的文化归属,又投射出法国文化自由奔放的情怀,双重的文化内涵融入作品其中,使《情人》一著享誉世界,使杜拉斯盛名全球。
三、多重文化内涵的融合
杜拉斯生活在20世纪初期,世界战争的爆发,世界殖民主义的猖獗,颠沛流离的时代,为其创作提供了特殊的时代背景;而童年时期在越南殖民地区生活的18年,在其一生的创作中,自觉或无意中都不曾停滞流露。杜拉斯通过“中国情人”的建构,创设了一个交织着多种不同文化、地域、和民族的特殊创作基调:从法国文化本位出发,以越南地域为依托,展开对东方民族文化的想象。这不仅仅是将异国风情推向了高潮,同时也因此而负载着多重文化关系。
第一层:法越之间的殖民关系。
法国XX借保护本国传教士的幌子,于1858年指派西班牙舰队进攻越南港口岘港地区,就此拉开了法国侵略越南,殖民印度支那的序幕。1867年占领越南全境,使整个越南彻底沦为法属殖民地。在法越殖民隶属关系当中,大多数法国人对殖民地充满对财富的渴望,也意味着印度支那会带给他们别样风情。《情人》中也这样写道:“对于大部分女人来说,有时对一小部分男人来说,到殖民地去的海上旅行,是一场真正的奇遇。”⑩(93)
第二层:中越两国邻友亲朋关系。
中越两国依山傍水,即为山水相连的邻邦,又同属于东方文明之中,在文化上的联系悠久而又密切。更古至今,中国文化不断传入越南,并加以吸收和改造。越南著名史学家陈重金说:“国人濡染中国文明非常之深……这种影响年深日久已成了自己的国粹。”⑾杜拉斯少年生活在越南,因此越南承担了“中国情人”和法国受众三者之间的桥梁,在杜拉斯心中,乃至世界人的意识里,越南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数千年的人口迁徙和文化沟通,促使中越成为邻亲近友。在杜拉斯的东方情结构建中,将中越文化塑造成如出一辙也不无理由。在中国情人创作中,杜拉斯显然将中国当做中越亲缘关系的一种外显,能更好的表现出东方文化之韵。
第三层创作中的中法文学关系。
中国题材和中国形象在法国的文学中层出不穷,杜拉斯也受其深刻的影响,她不知道面对东方这个未知的国度,该有怎样的态度和理解。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文学归属的矛盾和迷茫,她便把中国构建成具有神秘色彩的“理想国”,用以寄托真切的情感,重写记忆中的“中国情人”。
在越南、法国双重的文化身份下,构建想象中的中国情人。三种文化氛围的营造,两相交叉的东西文化交融,幽闭空间中的独处凝思,使杜拉斯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文化融合,这一切自然的交织呈现在作品当中。童年的特殊经历,法国文化的归属,在面对文化差异带来的焦虑的同时,敏锐的文学感觉和高度的文化包容,为其屹立世界文化民族之林提供文化支点。
四、杜拉斯“情人”的文化内蕴
情人形象几乎贯穿杜拉斯一生的创作生涯,在越南生活的那段时间里,这样一位情人是否真的存在?劳拉•阿德莱尔写的《杜拉斯传》中写到,杜拉斯曾在日记里记录了她在印度支那的生活,“雷奥”当地富有的安南人,但是他曾经出过天花留下过疤痕,相貌比较丑陋,但是衣着比较有品位。而《情人》中的情人,家境富裕、风度翩翩,虽有羸弱的身躯,但落落大方。为什么情人的形象会在杜拉斯创作中变形?为什么用近乎真实的口吻讲述“我”与情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在写作《情人》时,杜拉斯已70岁,能抛开更多的顾虑坦然面对越线的初恋,并不断美化中国情人形象,透过对情人形象塑造的变化,珍视自己返璞归真的自然情感。徐葆耕教授所说:“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回忆,它绝不是逝去的生活的简单复现,而是对往昔生活的诗话”。⑧中国情人形象的塑造承载着她个人情感的寄托,在反复的叙写下将埋藏内心深处不愿吐露于人的隐私折射其中。
一个重要的空间意象伴随着杜拉斯对异域情人的不断塑造,即单身公寓。正是这小小的房间,成了她的私人禁地,与外界割离,可以静心享受与喧嚣一线之隔的宁静。
“寝室里,灯光是蓝蓝的。有乳香的气味,在日暮时刻经常燃起这种香料。”⑨(31)
房间里幽暗的光线,弥漫着东方色彩的香料。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封闭、纯粹、私密的个人世界,不仅仅是白人少女的领地,也是杜拉斯的精神家园。单身公寓变成了杜拉斯欲望宣泄的的想象空间,“中国情人”则是杜拉斯的欲望指代。她将自己藏秘起来,将欲望的释放折射到情人身上,进行文学形象实践,这就是单身公寓特殊的场景,为其营造的私秘。在她的想象构建的世界中,单身公寓“被诗化”,为叙写中国情人形象,构建创作结构中的文化隶属创造了开放的空间。
肩负多重文化重担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创作中融合了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儿时记忆,也渗透着作为法籍作家自由、浪漫、奔放的生活情调,对中国情人进行建构和创作,倾其一生将创作穿梭于法越文化中,凌驾于东西文明之上,在创作中释怀自己寻找文化认同的焦虑和痛苦。
[1]劳拉•阿德莱尔著,袁筱一译.杜拉斯传[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
[2][3][4][6][7][9]王道乾,南山译.情人•乌发碧眼[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5](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M]//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徐葆耕著:《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下载提示:
1、如文档侵犯商业秘密、侵犯著作权、侵犯人身权等,请点击“文章版权申述”(推荐),也可以打举报电话:18735597641(电话支持时间:9:00-18:30)。
2、网站文档一经付费(服务费),不意味着购买了该文档的版权,仅供个人/单位学习、研究之用,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未经授权,严禁复制、发行、汇编、翻译或者网络传播等,侵权必究。
3、本站所有内容均由合作方或网友投稿,本站不对文档的完整性、权威性及其观点立场正确性做任何保证或承诺!文档内容仅供研究参考,付费前请自行鉴别。如您付费,意味着您自己接受本站规则且自行承担风险,本站不退款、不进行额外附加服务。
原创文章,作者:写文章小能手,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447766.cn/chachong/51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