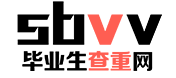摘要:“苦难”是文学写作中一种重要的叙事资源,迟子建的作品中始终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在脉脉温情中流露出爱和理解的人文主义之光。本文试从迟子建的小说出发,通过探寻作者关注的苦难境遇及采取的叙事策略,分析其苦难书写的独特性,对苦难叙述的悲剧精神及温情意义进行解读,反省其小说中的“苦难”书写所提供的写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背后的话语逻辑,在今天多元共生的文学视野里如何观照现实生活,从而获得一些对于当下文学写作的启示。
关键词:迟子建;苦难书写;独特性;书写困境;价值意义

“苦难”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之一,所谓苦难,“从个体角度可理解为现实苦难和精神苦难,即个人生活中的艰难不幸遭遇与精神上的本质困境;从社会角度来看,则可以理解为诸如贫穷、动荡、战乱等社会苦难和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等带来的大地灾难;而在哲学中,苦难可以看作是人类存在着的本质困境和永无止境的痛苦遭遇。”[[①张宏,《新时期小说中的苦难叙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1页。]]文学对于苦难的关照并不是消解苦难,而是通过对苦难进行解读与转化,让苦难的意义凸现出来,从而实现精神上的拯救与超越。因此,作家如何看待苦难,如何言说苦难,如何让肉体的苦难转化为精神的财富,使痛苦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则显得尤为重要。迟子建作为当代备受关注的作家之一,其三十多年的写作之中不乏对小人物、个人、社会乃至自然界苦难的写照,她的写作风格自成一家,温情中饱含人性之光,对于当下的写作则有着独特的意义。
一、迟小说中苦难书写的独特性
(一)乡土情结中对苦难的弱化
迟子建出生于北极村,因此她的文字自然而然的染上了这极北之地的风土与人情,从《北极村童话》开始,她的小说总不离故乡风物的描写,在这里有如精灵般飞舞的皑皑白雪,有原始富饶的森林,有美丽神秘的俄国老奶奶,有金黄香甜的苞米面粥,人们傍水而居,期待着破冰而来的渔汛与篝火,通过捕捞和放生那神秘的蓝色泪鱼来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这里的人们太多的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过着封闭、原始却安详、温暖的生活。与此同时,故乡热闹欢乐的节日、丰富多彩的民俗与传说也在小说中触目可及,通过这些作品,迟子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亲切、温暖、诗意与充满人情味的故乡世界。因此,在这些小说里,苦难并没有显露太多残忍的色彩,作者从民间的文化氛围和世态人情入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苍茫与空灵、浪漫与忧郁相互交织的苦难人生,在情景交融中放慢了小说的叙事节奏,在对童年、对故乡的回忆里,弱化了人世的悲哀苦痛,让人感到的只是一种淡淡的忧伤。
如《逝川》一文,在阿甲渔村,打捞泪鱼是一年一度的大事,甚至有一种传说:“泪鱼下来的时候,如果哪户没有捕到它,一无所获,那么这家的主人就会遭灾,因此“如果不想听逝川在初冬时节的悲凉之声,只有打捞泪鱼了”,但就在捕捞泪鱼的这一天,吉喜被央求去为村子的女人接生,在捕捉泪鱼还是为产妇接生的两难境地时,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冒着会遭受苦难的危险,不离不弃的守在产妇身边。当她终于忙完赶至岸边时,一年一度的渔汛已经过去,而她是全村唯一一个没有泪鱼可放生的人,正值孤独绝望之际却惊喜的收到善良的村民们送来的蓝色泪鱼,使所有的矛盾与困境都消融在人性的拳拳善意之中。吉喜因爱和善良陷入两难的境地,最后同样是他人的爱与理解为其化解,小说不禁隐含了这样的判断:人性中的善和爱意是拯救苦难的最终途径。在作者看来,阿甲渔村的人“只能守着逝川的一段,守住的就活下去、老下去,守不住的就成为它岸边的坟冢,听它的水生,依然望着它”,平凡之中不免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可即使面对苦难清贫的人生,他们却依然向善,坚韧且顽强的活着。整篇小说情景交融,作者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为读者构建了凄美而幽远的精神家园,使人忧伤却不感到绝望。
除此之外,作者也有意通过孩子或弱智者的视角去消解苦难的沉重,让灰暗的世界在孩童纯净的心灵下无所遁形。不管是《雾月牛栏》中的宝坠,还是《清水洗尘》中的天灶,亦或是《北极村童话》中的迎灯,作者都以孩子或“傻子”的视角来进行叙述,将故乡的民俗传统与故乡人的生存状态巧妙的投射到孩子的视界里。孩童纯净无暇的心灵让我们领略到了童年与故乡的美好,天空、云彩、大河、牲畜甚至是一草一木都充满了童真童趣,他们身处人生的苦难之海,却独立于苦难诗意的活着。作者用“傻孩子”兼作故事的叙述者,运用儿童视角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独特的诗意世界,在这些作品中并不存在冰冷的理性说教和客观的道德评判,而是在童言无忌中悄然展露苦难的残忍与人性的真实,在有着自然缺陷的人的纯真天性里,让我们看到所谓健全人的人格上的缺陷,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清醒着的人在苦难面前的自我救赎,充满了至纯至善的人间温情。迟子建一次次的书写故乡、童年、孩子,则是试图告诉我们人性中的纯美不可失去,不管人生具有怎样的苦难和缺陷,都需要美好的幻想与憧憬来支撑人们生活下去。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充满温度的,对于苦难的叙述也是拿捏恰当的,她的书写不像许多作家执意刻画的那种沉重到令人喘不过气的压抑与痛苦,而是在对故乡、童年的人与事的怀念中穿插进了苦难描写,同时对叙述节奏的控制与抒情化的描写也从另一个层面上消解了苦难、死亡等事件的血腥与沉重,使苦难蒙上了一层温暖的色彩。比如《白银那》一文中,在面对卡佳之死时,本应是灰暗阴冷的色调和恐怖阴森的场景,作者却别出心裁,营造了一种宁静祥和的氛围:为卡佳做棺材的声音是美妙的,“锯声悠扬,斧声清脆”,“她眉心上的那颗痣被阳光照得泛出钻石般的光泽”,抒情化氛围的营造与叙述节奏的巧妙控制,使苦难隐去了其中的残忍和冰冷,从而凸显了人性的光辉和温暖。
(二)史诗叙事中对受难精神的呈现
迟子建创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包括《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越过云层的晴朗》、《群山之巅》等,在她的众多长篇中,有三部作品具有典型的“史诗”追求:《伪满洲国》、《白雪乌鸦》、《额尔古纳河右岸》,分别在13年、几个月、近百年的时间跨度里书写伪满洲国历史、哈尔滨鼠疫灾难史和鄂温克族兴衰史。这三部作品之所以具有“史诗”的品格,不仅仅在于作者描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和生活场景,更重要的是书写了历史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和面对灾难时的精神历程,通过对整个人物的描述不动声色地将时代悲痛溶入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之中,在自然与历史的兴衰交替中完成了一次次贴近大地的苦难行走。
《白雪乌鸦》创作于2003年,是以1910——1911年秋冬之际在东北哈尔滨爆发的鼠疫为背景所创作的一部地方志式的小说,通过描写哈尔滨傅家甸地区的百姓在鼠疫爆发时遭受的苦难来反观这段历史中人物的精神面貌。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没有塑造民族英雄,没有呼天抢地渲染悲苦氛围,只是冷静地刻画在死神来临时人们的精神状态。正如作者在小说后序中所说:“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屡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小说出场人物众多,大到防疫的官员、医生,小到乞丐、水果摊摊主,但作者始终着墨于王春申、翟役生、翟芳桂、于晴秀、喜岁等“小人物”的书写。在这些普通民众身上,他们大都有着或大或小的来自精神和肉体上的伤痛,翟役生因为贫穷从小就被送进清宫里当太监,肉体的残缺、精神的奴役使他致死都活在“不完全的人”的阴影之下,而他的妹妹翟芳桂也在贫穷、战乱之中一度沦为妓女;王春申的妻子吴芬尽管再泼辣刚强、与金兰斗得再狠,却始终迈不过不能生儿育女的坎儿,至死抱憾终身……尽管每个人都默默承受着或大或小的伤痛,却仍旧有属于老百姓的那份善良与质朴,逆来的,顺受了,受不了的,便随着天灾一同离去。因为死亡如家常般频繁上演,索性过好当下的日子,于是“他们倾其所有,买酒买肉,狂吃纵饮;买绸买锻,装扮光鲜;买柴买炭,将屋子烧得从未有过的暖和”,即使在面对不可预知的明天之时,也要活得热烈,死得平静。生命的残缺与脆弱在以死亡为常态的环境中被转化为内在的坚韧与豁达,平静地接受人生的无常。
除此之外,在迟子建的苦难书写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显得举足轻重。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描写鄂温克族历史的小说中,作者把对生死的理解、对自然的敬畏、对人性的赞美在人与大自然的相互关系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史诗。这部小说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的自述展开,讲述了该民族从伪满洲国开始到文革结束后近百年的兴衰浮沉,小说采用了清晨、正午、黄昏、尾声一天的叙事结构来描写,以此对应该民族百年来的不同历史时期,通过讲述她的家人、爱人与族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吟唱了一首游牧文明的挽歌。在这部小说里,对自然的尊重贯穿始终,鄂温克族人民住在用树木搭建的“希楞柱”里,眼望星辰月亮,耳听风声雨声,身穿用羽毛或袍子皮制成的衣服,喝的是驯鹿奶和桦树的汁液,活着时一切取之自然,死后通过风葬,使肉体和灵魂又一同回归自然,在这里,人们与自然为伴,一同悲喜。他们与大自然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还体现在对自然的呵护上:他们从不砍伐活树,只烧“风倒木”;每次迁徙总不忘把垃圾清理深埋、填平搭建房屋时挖出的坑……鄂温克族对于生命和自然的敬畏及其透露出的万物平等的生命意识让我们为之钦佩。其次,在大自然中孕育成长的鄂温克人身上也时时体现着醇厚的人性之美:妮浩萨满为解救他人于苦难的水火而不惜一次次以牺牲自己的孩子为代价;“我”的丈夫瓦罗加为了保护他人而死于熊掌之下;偷驯鹿的汉族人依旧得到了原谅,“因为饥荒而产生的偷是可以被原谅的”;马粪包间接导致了交库托伐的死亡,索性用自残的方式来进行赎罪……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之中,迟子建构建了一个灵性而美好的世界,在这里,自然与生命是敬畏的,而苦难和死亡也不再是痛苦的,作者力求用一种宽广的胸怀去传递一种豁达而宽容的人生态度和健康而道德的生活方式,并且表达了在现代文明进击下对传统文明逐渐失落的惋惜。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一生与附着其上的欢乐悲苦不过是过眼云烟,但那些在生命中闪现的宽容、忍让与爱却是我们永远不能失去的东西,这也是她一直想要传递的思想。阅读迟子建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对“善”的坚守和对“恶”的模糊几乎贯穿于作者的整个创作。在作者笔下,源于苦难而导致的人性的异化是可以被理解和被原谅的,他们人性中的丑恶或是贫穷所致,或是灾难所致,或是遭遇精神上的伤痛所致,因此作者慷慨的给予他们同情、宽容和理解,以人性之光去抚慰每一个或残缺或伤痛的灵魂。
(三)个人遭际中对苦难的升华
在迟子建的诸多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她创作心态的一种重要体现便是追忆,回忆童年,回忆故乡,回忆亲人,回忆大自然。然而回忆往往是与逝去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是无法重获的温暖,所以要用文字一次次地去追念那些人和事的美好,这与迟子建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迟子建童年时期与姥姥生活在一起,父母的缺席使她的亲情变得不圆满,当她成年时又相继遭遇父亲、丈夫的离世,自此生离与死别便成了作者挥之不去的内心隐痛,因此她的某些作品则是个人生活遭遇的写照。我们读迟子建的作品常常有种不经意的忧伤,这与作者本人的经历与对生命、对苦难的思考是分不开的,正因为洞察人世间的苦难,所以她着意于救赎的力量,用悲天悯人的情怀,让苦难在温情之中显得不那么残酷,让底层之中挣扎的那些力量显得敬畏而神圣。而个人生活经历与大众苦难的结合,有效的拉近了作者与作品人物的距离,使大众苦难的书写在作者个体遭际的视阈下更显真切与深刻,同时作者也在个人与底层大众的视角转换中有效地完成了对苦难的展示,怀着对民间弱势群体的体恤与关怀,深刻书写了底层人物的悲剧性生存状态。
作于2006年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正是她在丈夫逝世后创作的一部带有个人色彩的长篇。这部小说讲“我”的魔术师丈夫死于一场意外车祸,“我”为了履行与丈夫曾经的约定,独自去三山湖旅行,途中因火车抛锚去了一个叫乌塘的小镇停留。“我”在这里邂逅了蒋百嫂、陈绍纯等人,并在目睹了这个小镇底层人民的悲剧性生存状态后,来到三山湖,在一个夜晚中放出了蕴含丈夫胡须的河灯,终于获得勇气与他永别于清流,从而释怀了丧夫之痛。这部小说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精神力度,是因为它不单单是作者伤痛的个人展览,而是将个人创痛与变幻的时代中的他人的遭际相互交织,向我们展示了比自我伤痛更为深重和广大的民间苦难,它的一字一句,真正的让作者与作品中人物的情感相通相融。
乌塘地如其名,煤窑众多,空气污浊,仿佛有永无止境的黑夜,而生活在其中的乌塘人的辛酸和苦难,却是比黑夜还要寒冷和绝望:在这里有孤苦伶仃的小食摊摊主,他的妻子被兽医老周输液致死;有在矿难中死里逃生、再也不肯下井的周二哥;有穿着光鲜亮丽的“嫁死女”,她们准备好保险单,上好节育环,为了高额的死亡赔偿金嫁给乌塘的矿工,却时时刻刻巴望着丈夫下井时能够出意外,从而获得一笔匪浅的收入;有爱唱丧歌却被朋友出卖、受家人冷落的画店老板陈绍纯……“辛酸的人海了去了”,这时候“我”看到了寡妇蒋百嫂:她“目光迷离、神态懒散、步态踉跄”,如“鬼”般从街市上穿行而过,她是镇上有名的耍酒疯的“浪荡”女人,常常如狗般蹲在深井画店的门口,在陈绍纯的丧歌中泪流满面,尤其每至停电的夜晚,便歇斯底里地发疯,叫骂着、哭喊着这世界上寒冷的夜。“我”在一个偶然的机遇里走进了蒋百嫂的家,却在那里看到了真正的人间地狱:在那把挂着大锁的木门背后,蒋百嫂的丈夫蜷缩在冰柜中,尸体早已损毁不堪。至此,“我”终于理解了蒋百嫂的种种失常,明白了为什么乌塘那些领导如此惧怕蒋百嫂,明白了蒋三生脸上的忧郁神色,原来黑夜里隐藏的是一场惨痛的矿难的真相,蒋百嫂生不能坦白相告,蒋百死不能入土为安,面对如此血淋淋的事实,“我”不堪重负沉默着离开了乌塘,去往三山湖。在这里我又遇到了同样具有伤痛过往的云领父子,在目睹了如此多的人间苦难之后,“我”开始审视自身的遭遇,不再埋首于自哀自怜,于是在温润的月光下,“我”放出了蕴含着丈夫胡须的的河灯,终于有勇气与丈夫永别于清流。至此,作者的个人苦难在残酷的底层现实面前获得了自我救赎,不再是个人伤痛的单向展览,而是在更为深重的民间苦难中让我们明白:人生不易,每个人都在痛苦与希望之间挣扎,只有珍惜当下,直面惨淡的人生才是对活着最好的诠释,对逝者和自己最大的安慰。
在这类作品中,作者倾心贯注的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通过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来反观生命、存在与抗争的意义,她想要传达的并不是苦难的深重、抗争的虚无、人力的渺小,而是绝望之中的温暖与希冀。即使在一个充满不幸的小人物身上,我们依旧能看到属于小人物的惊心动魄,或许只是一种情怀,或许只是一线希望。在《门镜外的楼道》中,当年迈的楼道清扫员小心翼翼的用六个鸡蛋来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在面对世人的流言蜚语也无悔追求爱情时,我们为之动容;在看到《亲亲土豆》中罹患绝症的丈夫对妻子的那份体谅与深情时,我们为之感叹;即使身处文革的寒流之中,《花瓣饭》中父亲与母亲之间的担心与爱护依旧让我们心头一热,甚至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那条守望蒋百的老黄狗,也在冰冷而绝望的寒夜中带给人一抹温暖。作家个体的生命体验使作者认识到生死的无常,而当她注目于那些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普通民众之时,她又看到民间这个更为深重的苦难之海,在作家的主体意识与责任心的约束之下,迟子建满含温情地对人世间的苦难进行了诗意的祈祷,为他们谱写了一曲曲生之赞歌,将所有的矛盾和龌龊消融在人性的拳拳善意当中。
二、迟苦难书写特点的形成原因探析
(一)地域文化影响
迟子建曾在一篇序言中说过:“每个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江河。对我而言,黑龙江、呼玛河、额尔古纳河就是我的生命之河,感染它们的气息也就浓些。”对于迟子建而言,故乡的山川河流、草木生灵便是她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而她笔下的那些在苦难中起舞的人们就像大自然的一年四季,有春的温暖,夏的热烈,秋的静美,也有冬的凛冽,可即使在冰天雪地的寒冬中,生命的力量、人性的美好仍旧生生不息,苍凉却强大。迟子建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故乡与童年影响了她的一生,因为生长在黑土地,热爱它,所以她的笔触更多的伸向了它,故乡壮阔的大自然,古朴的民风,以及那片冻土上发生的生与死的故事或多或少的都出现在她的文字里,正因为童年、故乡与故乡的人事在她的生命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美好,所以作者的苦难书写中一次次的将故事的发生背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习性及精神特点都定位在了东北那片黑土地上,从此笔下温润的月光,奔腾的江河与灵性朴实的生命体成为了她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繁衍生息的鄂温克族与萨满文化也是她创作中的灵感之源。鄂温克人信仰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人与自然乃是水乳交融的一个整体,他们对自然的敬畏来自生时一切取之自然,死后肉体与灵魂一同回归自然;在对待生死的态度上萨满文化也与我们大不相同,他们认为生死是一种阴阳图式的转换,死不是生命的终结,只是肉体的消弭,人死后灵魂便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另外,对神明的信仰也是萨满文化的一个重心,在萨满教义中,人与神灵相融相通,人类的一切活动皆被伟大的诸神所掌控,只有生前尽心向善,才能在死后不被诸神所惩罚。迟子建也曾在一篇序言中写道:“世上的路有两种,一种有形地横着,供人前行徘徊或者倒退;一种无形地竖着,供灵魂入天堂或者下地狱,在横着的路上踏遍荆棘而无怨无悔,才能在竖着的路上与云霞为伍”,这种生死观大概也离不开萨满文化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吧。迟子建的小说中崇尚自然原始的生命状态,其中不乏死亡的书写,她笔下的万事万物也都充满着灵性的丰采,即使面对底层的沉忧隐痛之时,也是诗意的祈祷与救赎。因此,不得不说,萨满文化对迟子建灵性优美的文学风格、豁达乐观的生命意识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作家个体生命体验
“所有的苦难感受,都是以人的视阈,以人的主体意识为出发点的,因此它最终势必是人的精神层面的反映。这种反映也表现在文学层面。同时,经过文学的审美化和抽象化处理,对苦难的叙述往往会和文学家们特有的人文关怀和对苦难的深度思考联系起来,同时为作品镀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而这种悲剧的指向几乎最终都是对于社会、民族文化乃至人性的反思”。迟子建的笔下不乏人间疾苦与生老病死,这与作者切实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她从小生活在亲情不圆满的家庭之中,成年后又不断遭遇亲人、爱人的死亡,而在东北那片寒冷的黑土地上,死亡与贫穷如家常般上演,面对苍茫的宇宙,人类不过沧海一粟,穷尽一生的那些爱恨离愁与困顿挣扎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因此迟子建始终努力以一种平静豁达心态来面对世事,力求以人类血液中流淌的温情与爱意来对抗人世间的寒流与绝望,体现在她的作品之中则是众生面对生死的豁达,应对苦难的平静,作家主体对每一个在逆流中行走的人给予的宽容与理解。以温厚的人性之光来抚慰伤痕累累的灵魂,这是一种基于对生命的守护、对人生虚无的抵抗而产生的具有博大内涵的人道主义精神。正如作者所说:“一个被冷风吹打了半个世纪的人,一个在写作中孤独前行了三十年的人,深知这世界上的寒流有多刺骨,也深知这世界上的温暖有多辽阔。”
(三)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承续
俄罗斯文学传统对于迟子建的创作也有很大影响。20世纪初中东铁路建成,大批俄罗斯人来到东北,随之也带来了充满异域风情的俄罗斯文化,而迟子建生长的北极村,与俄罗斯仅隔一条黑龙江,因为东北边陲与俄罗斯有着相似的自然风光与生活体验,因此迟子建相较于其他地区的作家来说,更易于与俄罗斯文学产生精神共振,无形中也便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此外,迟子建阅读了大量俄国作家的作品,其中不乏屠格涅夫、契诃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的优秀作品,而这些文学大师无疑对她的文学精神产生了或大或小的滋养与补充,正如迟子建所说,这些伟大的作家作品“都弥漫着苏俄文学所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人道主义关怀、宗教情怀、苦难意识,都闪现着博大深沉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品格”,这种温情书写传统的承续成为迟子建后来创作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即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通过文学来观照底层困境,力图通过发掘人性中的真善美来传递温情与希望,从而对抗底层大众的生存苦难与精神苦痛。但相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苦难书写,迟子建的书写则略显苍白与无力,对人性的过分唯美化与理想化的塑造,使作品从某种程度上缺乏对人物形象的深度刻画与人性内涵的多维剖析,从而导致了悲剧抗争美与现实批判意义的缺失。
三、迟苦难书写的困境探析
迟子建的苦难书写展示了底层的生活的艰辛与无奈,通过叙述民众在面对生活磨难和命运打击时表现出的顽强和坚韧,从而捕捉到闪烁的人性光辉,以此达到对苦难的超越,这是我们阅读迟子建众多作品时的一个整体感受,然而在沉重的苦难面前,我们不禁存在疑惑:诗意和温暖真的能够彻底化解深重的民间苦难吗?在关乎生死荣辱及自身切实利益之时,人类真的能够战胜人性的劣根吗?所有的价值判断仅仅能够归结于大写的“善”和小写的“恶”吗?类似的言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表达经得起一再书写吗?本文将从悲剧抗争美及温情救赎两个方面对迟子建苦难书写存在的困境作一浅要的分析。
(一)悲剧抗争美的缺失
细读迟子建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她所描写的人物在面对苦难时采取的更多的是一种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人生态度,没有主体对不幸命运的抗争与拯救,没有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哲理追求,没有对于苦难的剖析和解读,仿佛不幸和苦难就该天然的降临到这些底层中的小人物身上,因此人物性格与精神境界稍显单薄与系统化,也使作品主题缺乏了悲剧的抗争意识。
以《树下》一篇为例,主人公七巧失去母亲之后被过继到了姨妈家,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她变得沉默寡言,冷漠疏离,同时她却用自己充满灵性的眼光审视着周围的世界。但苦难并没有止步于此,在长久的预谋中姨夫强暴了她,死亡与苦难的接连上演使七巧始终在梦境与现实之中徘徊,一生抑郁寡欢。整篇小说意境清远,迟子建依旧构造了一个被淡淡哀愁包裹的诗意世界,让我们看到人性之美对苦难的再一次救赎。可是在阅读文本时我们不禁疑惑:在姨夫一次次的性侵中,七斗为什么没有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进行反抗,没有呼天抢地的哀恸,没有咬牙切齿的痛恨也就罢了,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态促使她最终原谅了十恶不赦的姨夫呢?和谐温暖的人际关系与宽容善良的人格品质固然重要,但若一味追求人物的逆来顺受与苟安自适,抛却人性中对不公命运的抗争与理性适度的性格塑造,则会使作品主题与言说方式显得单薄而类同,禁不起对文本的详细推敲。
同时,作者在处理人物及事件关系时,总是倾向于以人性之光化解矛盾,甚至为所推崇的本真之情而超越道德的界限,为人物的行为寻找可被理解的借口与自我救赎的方式。在《岸上的美奴》一文中,小女孩美奴因身患精神病的母亲的行为蒙羞,便设计杀害了母亲,这样扭曲疯狂的人性迟子建却题为“给温暖与爱意”,即使作者塑造了一个善良美好、敏感脆弱的美奴,但仅仅因为母亲身患疾病,她的行为伤害了女儿的自尊心,就可以不顾人伦道德及法律的约束而弑母了么?这种行为何谈温暖与爱意?《白银那》中的马占军为了牟取暴利哄抬盐价,间接导致了卡佳的死亡,而当他幡然悔悟免费送盐之后村民与乡长都以德报怨原谅了他,作者如此处理文本无疑是想为苦难找个出口,让人性的美好再一次彰显其价值,可是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不仅缺乏对人物性格转变的必要铺垫,也使结尾显得仓促而缺少可信度,而且寄恶人的感化和救赎于无辜性命的受难和牺牲的理念则显示出作者的一厢情愿和价值维度的模糊。不得不说,一味追求温情之美与人性之美,对人性单维度的认知与理想化描写,使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因为不能立足现实而缺少客观的价值评判,从而使诗意与温情也缺少了恰当的载体而有失真实。
(二)不彻底的温情救赎
除此之外,作者执意刻画的温情诗意的世界使苦难消解了其存在的沉重价值,在“该挑破疮疤,往人类病菌伤口上撒盐的时候,她却不撕破那层人性温情脉脉的面纱,手腕轻轻一抖,就让过去了。这一让,就让过了惊心动魄的一种悸,让过了刻骨铭心的一种痛”[[①徐坤,《重重帘幕密遮灯——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写作》,《作家》,1997年,第8期。]]从而使苦难流于温情人生的表面,缺乏对受难者精神层面上更为彻底的救赎。
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为例,蒋百嫂之所以成为一个疯癫而“浪荡”的女人,源于蒋百永远不能入土为安的死亡对她造成的打击,“我”在目睹了蒋百嫂及乌塘的各种沉重苦难后,不堪重负从而离开了乌塘,离开既是突出苦难的重围,也是对苦难的漠视与逃离,面对乌塘人间地狱背后的腐败与罪恶,乌塘人选择默默承受,“我”同情之余只能选择逃离。当“我”在民间这个深重的苦难之海中中获得解脱,走向新的人生时,那些依旧挣扎在苦难中的底层百姓该怎么解脱?作者并没有给出我们回答,甚至没有指出一种途径。与此同时,作者这种将个体伤痛同整个时代、整个底层大众的苦难比较从而获得自我解脱的思路不禁让人质疑:因为还有更多不幸的人,所以我该感到幸运从而释怀苦痛?因为苦难是人生的常态,所以它的存在与人类平静的接受即是合理?真正刻苦的伤痛会因个体身处苦难的汪洋大海而消弭吗?尽管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个人伤痛在底层大众这个更为广阔的现实苦难中的自我救赎和超越,却并未指出底层苦难的救赎之路,这或许与当下写作中缺乏成套的批判现实的价值系统相关,使作者只能简单地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展示人类生存与精神上的本质困境,一次次的寄希望于人性中的善与美来消弭人生中的苦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对社会、民族文化及人性深刻的反思。
四、对当下文学写作的启示与意义
苦难作为文学中一种不可缺少的叙事资源,关注底层、书写人物的生存苦难和精神苦难一直是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文革”后的苦难书写中,苦难是和历史现实对人造成的精神伤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要体现则是“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对于那个时代及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人的伤痛的一种追溯与再现,对苦难的讲述主要通过重构历史场景来宣泄一种悲苦的情绪氛围,而作为载体的文学也有效的完成了对现实苦难的抚慰。然而当苦难在80年代中后期一批先锋作家的笔下,则显出了残忍血腥的意味,极端的情感冲击力与黑暗彻骨的人性之恶使作品弥漫着一股冰冷绝望的气息。譬如在写农民生活时,作家们只能看到他们极端的愚昧无知、自私贪婪,却忽略了底层百姓在长久的农耕文化中形成的那种淳朴与自然,看不到他们在社会转型中面对新思想、新文化时精神上的痛苦与博弈。90年代以降,苦难被还原到民间历史与乡土中国,作家更多关注的是那些在历史的夹缝里生存的个体际遇与人性异化,通过个体的命运遭际去透视底层人物在时代蜕变中的困境,这无疑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与思考价值的。作为一个在文学中行走三十年的作家,迟子建的创作也是不断蜕变走向成熟的,她的作品开始时如“一泓清泉,后来则像宽广的大河”,对苦难与人性的理解也一步步走向宽广与深刻,然而作者始终如一坚持的,则是于深重而无尽的人间苦难中开掘出一线希望,通过文学传达人性的崇高,以期达到对苦难的救赎与超越。
面对当下的底层生活及尖锐的苦难与冲突,作家想要凸显的是一滩血一把泪还是在血泪中努力前行,不忘初心的抗争者,想要揭露的是人性的无尽黑暗还是那些在现实与理想碰撞中的人的精神上的挣扎与苦痛,选择什么角度、以哪种方式言说苦难对作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但笔者认为文学对于苦难的观照应是作家在理性与责任感的约束下对人的一种体恤与悲悯,是在坚实、广阔的现实大地上对苦难人生的一种救赎与祈祷。“文学应该给人以向上飞升的力量,应该帮助孱弱的人们去超越庸常凄迷的现实,去实现人生梦想中的高贵与神圣”,而不是“带领人们不断地下坠,下坠,在苦难的现实中无奈、无助和绝望”[[①洪志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在这一点上,迟子建的苦难的书写无疑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她笔下的苦难显得节制而温暖,写出了底层平民在面对苦难和生死时的执著、宽厚和无边的坚韧,使苦难的悲切与生存之痛在抒情化的语境下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生活的诗意与人性的美好,在那里,依旧有爱、有温情、有感恩、有坚韧和公义。
值得一提的是,迟子建在进行苦难书写时,因为对于人性之美的执意追求,偶尔便容易陷入一种同情误区,缺乏清晰的价值尺度与理性思考,比如《月白色的路障》一文,当张基础发现他的梦中女神王雪琪在纯洁的外表下竟做着肮脏的皮肉生意时,梦想破灭的他便对王雪琪萌生恨意,从而开车撞死了她。在这篇文章,作者想要表现的是在金钱与梦想的双重撕扯下人类的精神异变,具有明显的贬义倾向,但若用一种毁灭性的行为来充当道德审判的力量,作为被利益驱使的大众中的一个,因为心中美好的破灭,便以走上一条法理不容的道路来回应心中的绝望与愤怒则显得偏执而疯狂。怀着悲悯的眼光去体恤底层大众固然值得钦佩,但在向弱者施与自己的同情心时不加理性的判断与思考的约束,则是一种虚无的同情心的滥觞,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应具有的关怀品质。虽然作者赋予了人物善良、正义的天性,却没有深入到“良心”的本质上,人物要克服的并不是外在生活的重压,更艰难的是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嬗变,这一过程是煎熬和痛苦的。只有写出了人物精神上所承受的这种煎熬和痛苦,小说才能摆脱以伤痛展览为主的表面式苦难,从而具有超越现实苦难的飞升力量。
总之,迟子建作为当代优秀的作家之一,她始终站在温情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处于苦难命运中的人们给予了极大关注,这样的写作立场赋予了她的文字温暖坚韧的品质力量,尽管她的创作不是尽善尽美,但她依旧在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时代的苦难境遇默默祈祷,为人性的迷失寻求救赎之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消费时代里,她的文字让我们看到救赎与希望,让我们始终相信人性的力量,相信爱与宽容总会超越苦难之海,带领我们突出重围,走出绝望,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1]迟子建,《迟子建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版。
[2]张宏,《新时期小说中的苦难叙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3]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4]苏童,《关于迟子建》,《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5]刘倩,《迟子建小说中对“生命圆全”的追求》,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5月第34卷第5期。
[6]吴雪丽,《从“苦难”书写看作家的叙事立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第11期。
[7]黄明智,《苦难的温情书写及其困境——论迟子建小说创作》,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8月第8期。
[8]徐坤,《重重帘幕密遮灯——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写作》,《作家》,1997年第8期
[9]丛琳,《迟子建与俄罗斯资源》,《北方文学》,2011年第8期。
[10]张永忠,《论迟子建底层写作的主题》,《戏剧之家》,2014年第2期。
[11]范晓东,《试论迟子建小说的苦难叙事——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为例》,焦作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12]孟繁华,《底层经验与文学叙事》,《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13]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14]李彩霞,《底层文学苦难叙事的美学表达与缺失研究》,鄂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1期。
[15]洪志刚,《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书写姿态》,《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下载提示:
1、如文档侵犯商业秘密、侵犯著作权、侵犯人身权等,请点击“文章版权申述”(推荐),也可以打举报电话:18735597641(电话支持时间:9:00-18:30)。
2、网站文档一经付费(服务费),不意味着购买了该文档的版权,仅供个人/单位学习、研究之用,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未经授权,严禁复制、发行、汇编、翻译或者网络传播等,侵权必究。
3、本站所有内容均由合作方或网友投稿,本站不对文档的完整性、权威性及其观点立场正确性做任何保证或承诺!文档内容仅供研究参考,付费前请自行鉴别。如您付费,意味着您自己接受本站规则且自行承担风险,本站不退款、不进行额外附加服务。
原创文章,作者:写文章小能手,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447766.cn/chachong/16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