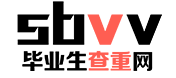摘 要
陈映真是X著名作家,忧郁与浪漫并存是他早期创作的一大特色。家道中落的窘迫、政治与文化的双重高压以及对鲁迅国民性思考的接受,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陈映真的早期作品便为我们呈现了忧郁与浪漫这对矛盾质素并存的文学现象。同时,陈映真早期作品中蕴含的研究意义也是丰富而深刻的。他通过底层劳动人民和市镇小知识分子这两类下层人物的视角,展现了理想与惆怅、希望与颓丧的交织,不仅反映了青年时期陈映真处于彷徨阶段的思想状况,也为其后期创作转型提供了更理性的思路、更新颖的题材和更多元的写法。
关键词:陈映真;早期作品;忧郁;浪漫
一、引言
陈映真,本名陈永善,是X著名作家。除了丰硕的小说成果之外,陈映真在文艺评论方面也有着深厚的造诣。
陈映真的著作中洋溢着热爱祖国和热爱中华民族的激情,被誉为“X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因此,文学界对他的研究越来越走向系统和深入。作为X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X岛内的文学研究者最先对陈映真及其作品进行研究。尉天骢发表了岛内第一篇与陈映真研究相关的文章,他从政治的角度探索陈映真的创作过程。詹宏志也是较早发现陈映真作品中有值得研究的能够反映社会问题的内容的研究者,不仅如此,他还意识到陈映真的创作与X文学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除此之外,陈映真在《试论陈映真》一文中以“许南村”为笔名,对自己进行评价和剖析,这对陈映真的有关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陈映真的研究逐步扩至大陆和香港,甚至也吸引了国外学者的关注。目前,可以帮助我们系统认识陈映真的作品、了解研究进展的综述有两篇。周建华的《文本、现实、创新——陈映真文学创作评论述评》,是在收集、研究关于陈映真文学作品的评论的基础上,着眼于创作的题材、思想以及手法,进行归纳和总结。王向阳则在《陈映真研究述评》一文中,针对海内外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总结。他认为,大陆对陈映真的研究有着系统完整、全面深入的特征,具体则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特点:研究视野的开拓、研究途径的创新和研究程度的加深。与王向阳的这篇综述进行比较,2006年之后关于陈映真的研究,方向大抵还是与王向阳“述评”里概括的特点相契合。研究者更偏向于用整体的眼光看待陈映真作品的主题、文本特点和其中的意义,内容上则更倾向于探讨乡土小说以及政治小说。
纵观文学界对陈映真的研究现状,侧重点大都放在陈映真牢狱生活中和牢狱生活后这段时间的作品上。诚然,苦难给陈映真带来了思想的觉醒,也带来了再创作的高潮,这一时期的作品固然有值得深究的思想意蕴。但陈映真的创作道路也不总是一成不变的。陈映真从小便接受了来自家庭的爱国教育,之后又经历了家道中落,这使他成了一名对祖国充满热爱、对劳动者报以同情的青年。因此,早期创作中弥漫着无穷忧郁的情绪,这是陈映真对理想和生活求而不得后的控诉。忧郁和浪漫,看似矛盾的两个质素,却在陈映真早期创作中常常并存。那么,这一现象在作品中是如何呈现的?产生这类矛盾风格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对陈映真早期作品的研究,对我们了解作者以及其后期作品转变会产生怎样的帮助?这些疑惑促使我想要探究陈映真早期作品中忧郁与浪漫并存的这一现象及其形成原因,进而了解陈映真青年时期的思想状态,以及早期创作对后期转型的影响。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忧郁与浪漫并存这一现象在文本中的描写,并分别从底层劳动人民和市镇小知识分子这两类群体的角度来分析。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陈映真早期小说风格的形成原因,是怎样的因素导致了忧郁与浪漫并存这一矛盾现象的存在。第三部分着重分析陈映真早期小说的研究意义,包括对青年时期陈映真思想状况的反应,以及对后期创作转型的影响。
二、忧郁与浪漫并存
(一)底层劳动人民的理想与惆怅
陈映真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其身上最独特的精神质素之一,就是拥有坚决而彻底的人道主义态度。他对底层小人物的同情与怜悯,在步入文学界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面摊》中,就流露出来了。而《面摊》作为陈映真的早期作品,典型地反应了底层劳动人民的理想与惆怅,以及其中的浪漫与忧郁。
《面摊》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一对有着底层劳动人民形象的父母,带着一个生病的孩子从家乡苗栗来到台北,靠着经营面摊来维持生计,然而却因怕警察没收赖以生存的“面摊”而提心吊胆地流动在城市街头。这对夫妇开市的第一天,就因为面摊经营得不规范而被抓进警察局,自此开始,面摊女主人与小说中善良的警官之间,便产生了交集。警局的注视、街头的微笑、找还面钱后怦怦直跳的心,陈映真通过善良的警察和清秀的母亲,将专政暴力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欺压,改写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与体谅。青年警察和年轻母亲那种近于爱情的关系,被陈映真塑造得温婉细腻、美丽动人。[1]除此之外,小说中的浪漫制造者,还有那个代表未来的孩子。孩子虽正咳着绝命的血,然而是否一定绝望,则毕竟仍属未知。但孩子是善良的、懂事的、纯洁的,当他看到“不抓人”的善良警察,便立志“长大了,要当个好警官”。在小说的最后,渐去渐远的“咯噔咯噔……”,营造出的韵味,正如“那颗橙红橙红的早星”,温暖而又充满希望。
《面摊》这样的小说题材,渗透着压抑的时代气氛,在X日据时代的文坛上是十分常见的,甚至于大陆三十年代的小说中也不少见。但是,陈映真笔下的警官与其他的这类小说中的各类巡查截然不同,他不是凶神恶煞、以鱼肉乡里为乐的,而是充满爱心的人道主义者。[2]警官的俊朗和温柔是陈映真重点描写的内容,“眼睛闪烁着温蔼的光”,甚至和其他“肥胖而暴躁的警官”形成对比,内心的善良与外在职责的冲突,暗示了警官对自己身份的厌恶和无可奈何,这也是他“困倦”产生的原因。
在《面摊》这篇作品里,一个最平凡的人的平凡困境,所表达的感情不是粗鲁的、浮于表面的,而是在那痛苦里面,还涌动着一股温馨的、深沉的人间爱。《面摊》中的忧郁,来自于这个平凡家庭的贫苦、来自于儿子的病痛、来自于时代的压抑以及阶级的压迫。但在陈映真的笔下,《面摊》还冉冉升起了一颗微温的“橙红橙红的早星”。年轻警官的善良、孩子的懂事、生活的平静、未来的憧憬……这些都是小说浪漫的表现。动荡的年代,底层劳动人民的理想不过是安定的日子,惆怅的不过是茶米油盐酱醋茶和躲不过的生老病死。
(二)市镇小知识分子的追求与颓丧
《试论陈映真》这篇文章是陈映真对自己的评价和分析,他在里面写道,“陈映真是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①,这也说明了在陈映真的作品中,市镇小知识分子会时常出现。
在社会动荡、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常常是一张显示社会起伏消长的动态晴雨表。他们的社会地位,远不及顶层的军阀贵族,也不至于底层的贫苦人民,而是处于一个可上至青云、可下跌深渊的中间位置。因此,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他们往往是心思最敏感、生活最忐忑的一个群体。这样一个群体,碰上时代更迭、世事变迁,他们的文化内涵、个人修养,使得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他们有理想,渴望以一己之力颠覆不安稳的现状,如此一来,他们的人生际遇难免充满坎坷,生活经历难免饱经沧桑。对于这样一个在社会中浮浮沉沉的群体,他们复杂的心态变化,自然成了作家予以关照的审美对象。作为市镇小知识分子的陈映真,他用文字探寻着这个群体的内心世界,刻画了几位忧郁而浪漫的知识青年:《我的弟弟康雄》里正值青春的康雄、《乡村的教师》里打过仗的吴锦祥、《故乡》里的海归“哥哥”等。
《我的弟弟康雄》以“姐姐”的意识流动为线索,双线交错,一条线写康雄的日记,一条线写“姐姐”的回忆,多方面地表现出康雄这位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心路变化。康雄是个富有爱心的市镇小知识分子,他渴望活在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那里安居乐业、人人自由、民主平等,而在这个社会里,他不以挣钱为目的创办了学校、医院、孤儿院,造福百姓。但这终究只是理想主义者的梦,梦醒了,现实中的康雄,不过是仓库里最平凡的员工。康雄租住在离仓库不远的窄小公寓,与母亲一般年纪的房东太太相恋、私通,产生了一种近乎“原罪”般的宗教感。为此,他一方面喘息于自渎的快感,一方面又为在一个妇人身上失去童贞而自责自咒,一方面追求虚无,追求那人生最深远最玄远的境地,一方面又逃不出宗教的道德榜样。[3]由于物质的压力和精神的压迫,康雄内心焦急忧虑,无处排遣。康雄绝望地颤叫着,最后选择结束短暂的一生,以此对抗残酷的现实。康雄作为知识分子,有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乌托邦理想是他的全部追求,是他心中最为浪漫的存在。当心中的乌托邦世界一旦破灭,康雄的忧郁便由此产生。康雄也试图反抗,试图追求虚无来摆脱忏悔,然而康雄最大的悲剧在于自己无法赦免自己,他认为自己的灵魂被不该有的肉欲玷污了,便再也没有资格去建立那些美好的乌托邦了。这样的忏悔、忧郁使他颓丧到无法翻身,推向他走进死亡的深渊。
《乡村的教师》,记载了X光复近于一年后发生在大湖乡里的故事。青年吴锦祥只身一人悄然归国了,成了乡村小学里的一名教师。五年的战火,几乎使吴锦祥对人性产生幻灭感,然而当他不可思议地活着回到这个山村,成为一名教师后,他的小知识分子的热情便醒了过来。他无声地呐喊着:一切都会好转的。
为人师的吴锦祥,经历过前线的生死搏斗,回到山村,面对着稚嫩的面孔,他燃烧着斗志,想以另一种身份报国,想以一己之力改造这个落后的小山村,“务要使学生们自己来担负起改革自己乡土的责任”。然而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他声嘶力竭地教学,仅仅换来了孩子们局促、无生气的状态。甚至下了学堂,看到的所有乡人都是懒散而无活力的,他像是在唱一出独角戏,渐渐地,他也开始堕落了,成了“一个懒散的有良心的人”。吃人的经历,将吴锦祥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击溃了。吴锦祥在学生应召入营的酒席上喝醉了,道出了在南洋当兵时吃人肉吃人心的经历,众人的反应,先是沉默,紧接着悚然,最后都噤着。故事很快就传遍了这个小山村,从此以后,吴锦祥遇到的全是异样的眼光,让本就对此事心怀愧疚的他更觉得自己罪无可恕了。他愈发虚弱无力了,终于选择了切脉结束这一生。浪漫的理想曾让吴锦祥也有积极向上的一面,然而忧郁的现实如末日的黑暗一般,遮盖了所有的希望。吴锦祥的死,让根福嫂悲恸,然而根福嫂的悲恸是仅限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恸。对于吴锦祥曾有过的理想,曾有过的浪漫情怀,这个小山村的人们无人知晓,也无从知晓,这里的氛围,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懒散、忧郁、毫无生气。
作为小知识分子的吴锦祥,由于读书,参加过抗日的活动;由于读书,对于底层的劳动者,他有着更强烈的感情和更深切的同情;由于读书,他被日军征派到处于战争一线的婆罗洲。战争曾迷惑他,让他以为人生来只为斗争,然而当他振作起来,试图用自己的理想拯救人们的懒惰,试图成为一位有所作为的改革者时,现实的种种,一点一点消磨着他的英雄主义,让他的理想沦为“幼稚病”,而战争中吃人肉的罪恶,使他的精神终于崩溃了。不同于康雄,吴锦祥的人生经历透着更为凄凉的气息,他的理想相对而言更接近现实,因此其命运的悲剧色彩更加浓烈。希望幻灭了,改革者吴锦祥陷入绝望,最后在无可遏止的颓败中走上自我毁灭的不归路。
《故乡》也是对市镇小知识分子的苦闷忧郁心态的真实写照。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哥哥”,家境殷实,本可以做一位高尚且赚钱的开业医师,但却选择在环境恶劣的焦碳厂做一位保健医师。他为贫苦的工人们治病,被认为是“大材小用”,但这便是他高尚的追求——只要能救人,他不在意金钱的多少,不在意工作的体面。“哥哥”满腔热情,也的确在焦碳厂救活了人。但那是个正在饱受社会转型之痛的X乡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无法回避的。家族的没落,冷却了他的热情。毋宁说,无忧无虑的生活才让他有了高尚的追求,如今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何谈追求?天使一般的“哥哥”颓丧了,最终成了魔鬼,成了赌徒。
陈映真的小说(特别是早期小说)便出现了几种声音在互相依托,互相辩驳,一种声音执着于某种本能的冲动,充满热情,渴望,既显现为对性与爱的饥渴,也表现为摆脱贫穷境遇的欲望,但这种受诱感的本能一开始便受到作家本人的压抑:他运用自小接受的一套文化话语、基督教的爱的理想、乌托邦社会主义、无XX主义等等来检视和审判自己本能的冲动,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些本能的巨大力量及其毁灭性,于是一方面隐晦含蓄地表现这些本能,一方面又沉思它的本质、趋向、力量,加以导引。[4]因此,康雄对性爱本能的渴望,在基督教的忏悔意识与乌托邦的压抑下,成了罪恶的源头;吴锦祥为了生存吃人肉,当这个秘密公之于众后,他对自己的检视和判断逼着他在矛盾中走向死亡;“哥哥”由于文化涵养产生了高尚的理想,又在家道中落后对摆脱贫穷境遇产生了本能的欲望,本能的巨大力量加速了“哥哥”的堕落。他们都胸怀大志,但终究敌不过铁板似的现实。悲剧的接连上演,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将理想付诸实施的勇气和魄力,更是他们对现实社会无声的对抗,当然,也是作者处于人生彷徨阶段的真实写照。
三、陈映真早期小说风格的形成原因
吕正惠是X著名评论家,他把1959年到1961年定义为陈映真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作家的创作往往是现实社会,乃至自己内心的一面镜子,而创作风格的形成,亦是和现实经历、时代的大背景、所受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
(一)家道中落的窘迫与迷茫
1937年,陈映真在台北县出生。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年纪尚小的陈映真看到了一个被侵略者蹂躏,即使光复也依旧混乱和贫穷的X。他的父亲是台中圣经书院的国文教师,是一个有爱国心的牧师。受家庭的影响,陈映真从小信仰基督教,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人道主义精神与爱国主义思想,因此,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理想是显而易见的。他将写作的笔触伸向最平凡的底层劳动人民,第一篇发表的小说《面摊》,便是寄同情于这生活艰难的小人物。带着咳血小儿的面摊夫妇,在繁华却也不安稳的台北街头谋生,陈映真并不想让这对夫妇的生活雪上加霜,便在小说里安排了一个有着人道主义精神的青年巡警。青年巡警的善良,在陈映真看来,正是现实社会所缺少的东西,也是作家应追求的境界、应书写的精神。
在《面摊》发表之后,《我的弟弟康雄》、《故乡》、《乡村的教师》等小说也陆陆续续得到发表。这些作品总是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窘迫和迷茫,乌托邦式的理想幻灭,小说里的人物紧跟着堕落或是死亡。浪漫与忧郁并存,可以说是陈映真早期作品中两个重要的质素,而产生这两个质素的原因,与陈映真家道中落的窘迫和迷茫是分不开的。
在陈映真九岁时,哥哥陈永真亡故。这位不管是外貌还是性格,都与陈映真极其相似的双胞胎哥哥的离开,给年少的陈映真蒙上了厚厚的一层落寞和感伤。1958年,他的养父去世,留下的一些遗产到了他读大学时也所剩不多了。这样的身世,在陈映真的青春时代留下了灰暗的烙印,浓重的感伤便倾泻在他的早期小说创作中。
于是,虚无者康雄(《我的弟弟康雄》)终于逃不过现实与道德的束缚,颤抖着撕掉自己的生命;想要改变社会的吴锦祥(《乡村的教师》)在现实中四处碰壁,现实的冷水泼灭了他的所有热情,迷茫一点一点地侵蚀他,直至死亡;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哥哥”(《故乡》)在经历父亲病故、家道中落的打击后,与从前判若两人,成了淫邪嗜赌的恶魔。这些故事发展是否合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在青春时代产生的忧郁苦闷可以通过文字的书写得以宣泄。破败的故乡、贫穷的忧愁以及远离家乡的思念,无一不在早期的小说创作中找到影子。而小说中的青年,总是怀揣理想但四处碰壁,这也是陈映真处于人生迷茫阶段的真实写照。
(二)政治文化的状况与压力
文学来自于社会,也反映了社会万象,因此,文学必定会表现出时代精神。在易感的青春期,陈映真经历了日据时代、“二二八”事件以及五十年代X的贫穷、落后和动乱,政治文化的状况与压力成了他早期小说风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1947年的“二二八”起义和1949年后国民党在X实施的政治高压、文化高压像阴影一般弥漫在陈映真周围。正如《面摊》这个故事,青年警察内心的善良和外在职责之间的冲突,是他之所以“困倦”的原因,也是那个时代极度压抑的政治气氛的象征。
陈映真“拼命爱国”的精神气质,从他步入X文坛后,便有所表现。位卑未敢忘国忧,因此,对于X当局的种种劣迹,对于X社会出现的问题以及X人受日据时期影响产生的思想,他都试图通过小说来拯救。他想用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来帮助小人物,他想拯救那些空洞的思想,他提出改革X社会的方案……在小说里,他大可以为这些人物创造一个美好的结局,以宽慰自己的心灵,但是惨淡的现实不得不让他清醒。五十年代X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革者,他们既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又受阻于自身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更经不起残酷现实的考验,于是陈映真以忧郁的笔调,结束了笔下每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生命。
除此之外,受政治环境的影响,陈映真早期小说中出现了现代主义思潮。50年代前夕,X援助X,除了提供了资本和技术,还为X文化界带来了现代主义思潮。当时,大陆30、40年代的作品被禁,X进步作家赖和、吕赫若、杨逵等的作品也被清除,X的文化领域瞬间如同一块空白,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于现代主义的到来,如同久旱逢甘霖,毫不犹豫地便收下了。[5]陈映真便是在这波文学思潮中踏上文坛,使得早期的作品更注重个人内心情感的表达,充满感伤忧郁的情调。
(三)对鲁迅国民性思考的接受
鲁迅小说也对陈映真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中学时代,他便读过鲁迅的《呐喊》,他这样说道:“我自此才看到中国的贫穷、愚昧、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全意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位炎黄子孙都奉献于国之自由和新生,那么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就有了。”②鲁迅的小说不仅让陈映真与爱国主义如影随形,还使他的作品中也出现了不少关于国民性的思考。
就《呐喊》中的作品来说,无论是《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白光》等,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鲁迅所营造的,介在封建传统与追求个人解放间的张力,那种深深被传统制约,人与人之间不自觉地互相迫害、伤害的文化人格与国民性。[6]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陈映真的早期作品中,无形地接受了鲁迅小说中对“国民性”的思考。同时,为了联系“国民性”主题,陈映真往往选择“重返者”作为他早期小说里的主人公,这和鲁迅早期的小说有极大的相似。例如早期代表作《乡村的教师》,陈映真用了不少笔墨来描写乡村里的人们,他们是主人公吴锦祥最熟悉的亲人,抑或是最亲切的邻里。然而当吴锦祥离开自己深爱的故乡,经历了战场上的生死一线,最后有幸活着重返故乡,五年的时间,他再次面对家乡人物时的感觉和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根福嫂还是那个爱子如命的母亲,她也一如既往地喜欢搬弄。意外归乡的儿子不仅和从前一样顺从,还得了一份体面的教师职位,这让根福嫂忍不住在众人面前有意无意地炫耀。这样的炫耀传入吴锦祥的耳中,难免是有些尴尬和不适的;而X乡下的农村小孩,在吴锦祥热情的课堂上,依旧是局促而无生气的,如同鲁迅笔下被封建社会消磨了一切灵性的闰土,然而闰土尚且承担着那个年纪该有的生活压力,他们却是处在无忧无虑的年纪;当吴锦祥道出吃人的经历后,寻求视、听觉刺激的人们把这个故事传遍了山村,并且投以吴锦祥异样的眼色。吴锦祥切脉自尽后,整个乡间对于这种凄凉,还是以一贯的隐忍、懒散的状态含糊过去,如同鲁迅笔下的看客一般,冷漠又残酷。小说中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陈映真对X人民“国民性”问题的思考。陈映真借着故事主人公的态度和立场,把围绕在主人公周围的亲人、邻居、孩子们在思想人格上的问题暴露出来,这便是陈映真早期小说中对鲁迅国民性思考的接受。
四、陈映真早期小说的研究意义
(一)反映青年时期陈映真的思想状况
所谓言为心声,作家在作品中持有的观点,较大程度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状况。陈映真的早期小说,为我们了解青年时期陈映真的思想状况提供了许多思路。
尉天骢说:“陈映真早期小说中的绝大多人主人公,一方面为青春期的情愫所困惑,一方面则追向梦想,这是一群物质上贫穷、精神上虚无、气质上浪漫的青年。”③这样的评价准确地阐释了陈映真早期作品中人物的思想特点,而这些思想特点,也是他对时代感同身受后的体验和深思。
正如作品中常常表现出来的那样,无论是在乌托邦中建立贫民医院的康雄、还是站在讲台上试图“使学生们自己来担负起改革自己乡土的责任”的吴锦祥、或是甘愿在焦碳厂当着不是那么得体的保健医生的“哥哥”,都反映了陈映真是一个充满理想和反抗情绪的穷苦青年;是一个在中国的动乱中迷失但仍然深爱祖国的X青年;是一个内心浪漫的热血青年。而悲剧性的小说结局,既是康雄们在无言抵抗着社会现实,也是作者深痛批判着时代病态。
陈映真的早期作品中不时流露出来的忏悔意识,也反映了青年时期陈映真的思想状况,即他对基督教中“忏悔”这一教义的体会。这种与宗教有关的心理,在《我的弟弟康雄》这篇小说中得到了直接的描写。与房东太太的私通,让康雄的内心被“原罪”般的宗教感充斥着。在这之后,康雄因为不能忍受自身的污浊而产生了内疚感,便企图通过忏悔求得精神的安慰和解脱,以至于死之将至,他绝望地在日记里写道:“我不曾想到向来追求虚无的自己,时至今日仍逃不出宗教的道德的律。圣堂的祭坛上悬着一个挂着基督的十字架。我在这一个从生到死丝毫没有和人间的欲情有分的肉体前,意识到享受至美已经与卑污的我无关了。”④显然,是认同基督时带来的不由自主的反思成了康雄觉悟的原因,而非外界的议论或社会的规范。陈映真虽是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但他无时无刻不关注着X的实际情况,不曾脱离过现实。当时X苦难的现实让这些人渴望被上帝救赎,殊不知,忏悔的归宿不是颓废,就是自毁。忏悔并没有让忏悔者得到解脱,再加上无法企及的救赎,使得忧郁与苦难的程度丝毫未减。这样一来,小说文本中浮现出来的忏悔意识,沾染上了伤感的基调和强烈的情绪,真挚诚实地描述着陈映真青年时期的忧与思。
陈映真是位“拼命爱国”的作家。受鲁迅创作的影响,他开始思考国民性,他寄理想于书写,希望能通过书写唤醒人们,驱赶无知,看到市镇小知识分子站起来的那一天;他狂热追求着理想,对残败不堪的社会现状仍抱有浪漫的态度,但家道中落的阴影、政治文化的高压、国民的劣根性,这无穷无尽的碰壁让这位市镇小知识分子不堪重负,无穷忧郁的情调由此产生;接着,他试图用基督信仰和人道精神抚慰自己伤痕遍布的忧郁心灵,然而这种方式无法从根源上“治愈”。
吕正惠教授认为,1959年到1961年是陈映真创作生涯中的自传时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与陈映真有极大的相似处,即都是有着浓重感伤情绪的市镇小知识分子。透过他的早期作品,足以看出青年时期的陈映真,正处于人生彷徨阶段,他不缺理想,不缺抱负,然而惨淡的现实让他踌躇不前。
(二)对后期创作转型的影响
纵观陈映真的全部作品,他的作品风格一直随着他的思想变化发展。早期作品受现代主义影响,体现着多层次、多主题、象征主义等“现代”的一些特色,但早期作品只能在家庭纠葛、个人恩怨和内心世界的狭小天地里书写。随着陈映真思想的不断成熟,政治格局的风云莫测,他开始对现代主义的迷茫进行反思,并毅然举起了现实主义的旗帜。“他认为X需要出现一种给予遭受欺辱的、遭受践踏的、遭受漠视的人们以温暖的抚慰、以勇敢的斗争的乡土文学”。⑤于是,作为市镇小知识分子作家的他,受早期创作的影响,他依旧将目光放在下层人物身上,涉足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只不过,早期创作中弥散开来的忧郁、自怜的感情,被揭露、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他开始从更广阔、更理性的角度,审阅X的现实生活。
《将军族》可以说是陈映真转变时期的代表作,小说一反世俗之陈见,演绎了一出X姑娘和大陆老兵,即本省人“小瘦丫头”和大陆人“三角脸”之间的爱情悲剧。就作品的内容而言,叙述在X的“大陆人”和“本省人”的生活交集、感情纠葛,这是陈映真创作转型后的主要题材、主题和人物,从而表现了陈映真以文学作为反应社会现实的手段,鲜明而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这与早期创作中体现出来的主题新颖性有一定的吻合。《将军族》既反应了X士兵到老也没钱娶妻的苦况,也揭示了X穷人的女儿沦为妓女的惨状,[7]显而易见,这无疑是受早期创作的影响,使得陈映真在后期转型中依然同情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不仅如此,早期创作中由于家庭影响产生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一直延续到了后期创作中。《将军族》就充分表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寄同情于受损害、被侮辱的小人物,泄愤怒于黑暗、罪恶的周遭世界。[8]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充满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说贯穿于陈映真的创作之中。
在艺术技巧的运用上,后期创作的转型也受到了早期创作的影响。后期转型中,陈映真虽转向了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进行学习和继承,但早期受现代主义影响而吸取的象征手法并没有被他完全抛弃,而是通过将这两者合二为一,形成了陈映真自己独特的表现方法。这一点典型地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上,小说大量安排“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恋爱与结合,并孕育新生命,以此来象征和寄托作者对中华民族统一的理想。
对于后期创作转型,早期创作的作用可谓是供其精华,这些精华也正是陈映真作品里宝贵的特质。加之思想的愈发成熟,政治环境的愈加复杂,不同于早期创作中无尽的哀伤,转型后的作品不仅控诉了下层小人物的悲惨生活,更是对他们互助友爱的高贵品质的歌颂。它标志着陈映真已从知识分子顾影自怜的个人小圈子中冲出,开始走向广阔的现实社会。[9]
五、结 语
纵观陈映真的早期创作,忧郁与浪漫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质素,是普遍存在的。不论是底层劳动人民,还是略有见地的市镇小知识分子,对于复杂的现状,常常存在着希望,也伴随着绝望。而这种独特风格形成的原因,与作者的成长经历、与时代大背景、与受到的文化熏陶是密切相关的。早期作品中忧郁与浪漫并存这一现象还具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陈映真通过对现实的洞悉,记录真实的X、真实的时代,反之,透过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陈映真青年时期真实的思想状况,这也对学者们研究其后期作品如何转型起到很大的帮助。
参 考 文 献
- 李勇.X左翼乡土文学对大陆社会转型期文学发展的启示——以陈映真的文学创作为例[J].华文文学,2019,(151):49
- 张雁泉.试论陈映真小说中的人生救赎之路[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8(3):86
- 沙芜.陈映真的小说[A].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14)[C].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黎湘萍.X的忧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86
- 许永强.从仰望理想到人的异化——论陈映真小说的题旨[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3):34
- 黄文倩.陈映真早期小说对鲁迅的国民性思考的接受与衍义[J].台声,2019,(20):46-50
- 蔡美琴.从现代主义的迷朦到现实主义的追求——论陈映真的创作道路[J].广州研究,1984,(5):59-63
- 涂碧.试论陈映真创作的风格[J].当代作家评论,1984,(4):117-127.
- 蔡美琴.从现代主义的迷朦到现实主义的追求——论陈映真的创作道路[J].广州研究,1984,(5):59-63
致 谢
行文至此,我的毕业论文告一段落,我的本科生涯也即将落幕。静下心来,回顾过往的四年,思绪万千。四年的大学生活,不论在学习上,还是在社团活动、社会实践中,有太多的人帮助、支持我,给我的本科生涯留下美好的回忆。对此,我心存感激。
首先,我要感谢母校宁德师范学院对我的培养。作为一名师范生,我会铭记“使命、责任、追求”的校训,以此指导今后的生活和工作。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李欣池老师对我的指导与帮助。虽然到了大三才第一次上李老师的台港文学课,但短短一学期的课程,便让我对台港文学产生浓厚兴趣。毕业论文写作是对我专业知识与能力的最终考察。从选课题、查资料、列提纲、拟初稿,到最后逐字逐句的修改和完善,李老师始终认真负责地给予我指导,指引我方向。由于疫情,我与李老师无法当面交谈,但当我写论文遇到问题时,李老师总能在百忙之中及时回复邮件,为我解答。同时,也感谢林文等各位老师在开题期间的悉心指导,感谢四年来给我们上课的每一位老师。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五个可爱的室友。你们是我大学期间最形影不离的伙伴们,谢谢你们这四年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聆听和包容。
虽然学习的历程暂告一段落,但求知的道路却永无止境。我将学以致用,热情拥抱将来的每一天。祝愿老师们工作顺利,同学们前程似锦。
1、如文档侵犯商业秘密、侵犯著作权、侵犯人身权等,请点击“文章版权申述”(推荐),也可以打举报电话:18735597641(电话支持时间:9:00-18:30)。
2、网站文档一经付费(服务费),不意味着购买了该文档的版权,仅供个人/单位学习、研究之用,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未经授权,严禁复制、发行、汇编、翻译或者网络传播等,侵权必究。
3、本站所有内容均由合作方或网友投稿,本站不对文档的完整性、权威性及其观点立场正确性做任何保证或承诺!文档内容仅供研究参考,付费前请自行鉴别。如您付费,意味着您自己接受本站规则且自行承担风险,本站不退款、不进行额外附加服务。
原创文章,作者:写文章小能手,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447766.cn/chachong/851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