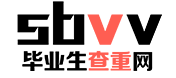内 容 摘 要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互联网与产业经济的深入结合,“网络平台+网约工”这一新型用工模式随之产生。网络平台用工模式将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需求与劳动力资源灵活有效地结合,促进二者共同发展。但网络平台用工模式拥有不同于传统劳动用工的特点,使得网约工的劳动关系认定成为挑战,网络平台公司和网约工的劳动纠纷也在不断产生。
为完善我国劳动关系认定,促进网络平台用工模式劳动关系的认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本文将梳理网络平台用工模式的类型和特点,结合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解析新型用工模式对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挑战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探讨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网络平台;劳动关系认定;劳动用工形式
一、绪 论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当今社会,我们国家的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网络平台也渐渐地与经济产业融合起来,网络平台+网约工这种新型用工模式兴起。据第4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较2018年底增长2598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1.2%,较2018年底提升1.6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较2018年底增长2984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较2018年底提升0.5个百分点[1]。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6.39亿,较2018年底增长2871万,占网民整体的74.8%[1]。
与此同时,网约工数量的增长,加之网络平台公司对网约工的不规范管理,使得网约工权益难以保障的情况大量出现。新经济形态的发展开辟了劳动力发挥价值的新方式,对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也发起了挑战,需要劳动法律制度予以回应。且探讨网约工的用工问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有利于全面保护劳工权利,以及促进网络平台用工模式的良好发展。
目前对于网约工的研究,主要探讨网络平台与网约工之间是否存在用工关系。刘文科和郑雯在研究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2018年第一季度中涉及网络平台用工责任的32件诉讼案件后发现,法院对于网络平台的用工责任有以下两种意见:一是肯定用工责任说,认为网约工与网络平台之间存在用工关系,网络平台应当承担用工责任;二是否定用工责任说,认为网约工与网络平台之间不存在用工关系,既然两者之间不存在用工关系,网络平台无需承担责任。
笔者认为:网络平台与网约工的用工关系存疑的原因,在于与重视身份从属性和经济依赖性的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不同,网络平台+网约工的用工模式下,网约工对平台的身份从属性较弱,对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的选择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且网约工的劳动者身份认定也因此存疑。在现有研究中,对于解决网络平台与网约工的用工责任以及网约工的身份认定问题,通常有两种观点:一是扩大劳动关系的司法解释,将网约工纳入劳动者行列中,纳入劳动法的调整和保护范围;二是在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中建立贴合新型用工关系特征的第三种关系。
虽然许多关键问题的认定以及具体的调整方法还有待商榷,但研究讨论网络平台+网约工用工模式下的用工关系和网约工的身份认定问题,使得我们在网约工劳动权益方面达成了一个共识:网约工的合法权益需要受到保护。而推动劳动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有利于推动新型经济形式和用工模式的良性发展。
(二)文献综述
学者胡珍和董斐在研究网约平台+网约工用工模式时,都重点探讨网络平台的用工形式特点以及平台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和用工责任。笔者认为选取“网络平台”为研究重点是可行的。现今都以经济产业和网络平台结合为主要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方式。互联网给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新的活力,及时了解网络平台用工模式,完善相关措施,有利于推动网络平台和模式的规范发展。
而刘文科和郑雯在研究过程中,主张先对网络平台用工形式的特点进行研究,再根据网络平台用工模式发展的新特点与传统劳动关系相比较,才能发现网络平台用工关系认定的困境并提出有效措施。笔者认为这种研究思路是科学的,并在本人的论文中,先详细描述网络平台用工形式的特点,以便后续的研究。而郑雯在《论共享经济模式下的用工法律规制》[2]中,则聚焦于网约工的身份识别,认为需要确定位网约工的法律身份,才能理清网约工与网络平台的法律关系,从而实现对网约工基本权益的保障和促进网络平台+网约工模式的良好发展。
认定劳动关系是否存在是解决劳动纠纷的前提,而明晰网约工和平台公司是否为劳动关系适格主体是认定劳动关系的基础。笔者认为可将刘文科和郑雯在《网络平台用工责任之类型化探析——共享经济为背景》[3]以及郑雯之《论共享经济模式下的用工法律规制》[2]的行为思路结合起来,先分析各式用工形式的特点以及平台公司与网约工的劳动关系实质,接着聚焦网约工的身份识别争议,探究网约工应得的法律身份及其对劳动关系认定的影响。
而为何“网络平台+网约工”用工模式下网约工的身份劳动关系认定存在困境?Kassi O, Lehdonvirta V.认为,随着经济和互联网科技的不断结合,传统的用工模式被在线平台的工作逐步补充或替代。在线劳动力的使用近乎实时表现在主要平台上发布的任务,与传统劳动力市场的服务模式存在着明显不同[4]。
笔者发现:在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应形成劳动关系,且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有较强隶属性,需要听从用人单位的安排,在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进行劳动,用人单位给付劳动报酬。孙秀则指出了“网络平台+网约工”用人模式的特点:在主体之间的关系来看,从传统的紧密隶属关系走向松散;网约工可注册多个网络平台,向多个网络平台同时提供劳动,出现多重劳动关系;从劳动基准条件来看,平台模式下,网约工可自行选择工作时间、地点、工作内容,且一般自备生产工具;劳动报酬的支付也相对复杂。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未能囊括新型的用工情况,使得网约工的劳动者身份存在争议,“网络平台”劳动模式的劳动关系认定走入困境。新型用工模式已经对传统的劳动关系认证标准发出了挑战。
周贤日提出:灵活松散的新型劳动者应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之内。林嘉教授则提出: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经济的高速发展,二者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于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非常重要。在适用劳动关系从属性标准的实质性内容去判断劳动关系时,判断过程中要综合全方面考虑各种因素,使得判定的标准更加细化且具有可操作性
董保华教授指出:为更好解决当前劳动关系认定中出现的难题,可借鉴英美法系的理论和法律时间,从立法和司法两条路径入手。立法时应优先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为新型就业模式下的劳动者提供基本的权力保障是XX的职责。而在司法方面,应加强实施动态监管,包括发布服务标准和治理规范及改善社会监督,支持平台公司加强内部治理和安全,总结有效案例的推进,审查具体案件时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分析上述见解可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其与经济的不断结合,网约工数量会越来越多。“网络平台+网约工”模式中存在的非标准劳动关系可否被认定为劳动关系以及应该如何进行保护,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世界性难题,目前国内外都在展开不同程度的讨论和研究。笔者认为:法律应尽早进行调整,将网约工这一群体纳入法律保护之下,使得网约工的基本权益得以保障,网络平台+网约工用工模式可良好发展。虽然具体的调整方法尚未达成共识,但总体来说,世界各国在网约工劳动权益方面都达成了一个共识:网约工的合法权益需要受到保护。
(三)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了解各类网络平台的各类用工形式和用工特点。通过文献调查和研究,笔者聚焦于依托互联网而生长的网络平台公司,发现网络平台的用工模式有以下四个特点:用人关系主体发生改变,生产资料提供方自主性增强,企业管理和网约工提供劳动的方式更为灵活,劳动报酬的支付形式更加复杂。在了解各类互联网平台的特点后,需要进一步通过文献分析和文献研究,了解各类用工方式不同的互联网平台是否存在网约工的用工关系,互联网平台是否存在用工责任。运用个案研究法后,笔者发现:对于当今社会互联网平台与网约工是否存在用工关系这一问题,司法界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肯定用工责任说;二是否定用工责任说。而笔者认为互联网平台与网约工之间存在用工关系。为了证明“网路平台与网约工之间存在用工关系”这一观点,笔者将以“网约工的劳动者身份认定”为研究重点,验证网约工可被认定为劳动者,以佐证互联网平台与网约工之间存在用工关系。通过文献分析和个案分析,笔者了解到:与重视身份从属性和经济依赖性的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不同,网约工对平台的身份从属性较弱,对工作内容、时间和任务有一定自主选择权,且有相当数量的网约工自备生产资料参加劳动,劳动报酬的给付方式也有了更多种灵活的形式,但尚对互联网平台有较强的经济依赖性。新型用工模式中多种不同于传统劳动关系的特点出现,无疑对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发起了挑战。社会对网络平台用工形式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尚未达成共识,为了推进新型用工模式的两性发展和推动实施对劳动者的全面保护,笔者将通过文献调查和文献研究法,探析国内外相关文献,寻找可供借鉴的方法,并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提出理性反思。
(四)研究方法
文献调查法查阅文献,收集资料,了解网络平台劳动用工形式及劳动关系难以认定的原因或影响因素。
个案分析法针对特定用工形式开展个案研究,深入研究这种用工形式下劳动关系难以认定的原因或影响因素。
(五)论文结构
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分析网络平台的劳动用工形式和劳动关系认定这一议题的研究背景,以及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再通过解析国内外文献,参考国内外学者对本议题的研究方向,确定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
第二部分是分析网络平台的劳动用工形式。首先简单介绍网络平台,再探析网络平台用工形式的分类和不同用工类型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引出司法界对于网络平台的用工关系争议。
第三部分是探析网络平台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首先分析清楚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再分析因劳动用工形式与传统用工形式不同,而带来的网络平台劳动认定关系存在的困难及对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挑战。
最后部分是提出网络平台劳动关系认定的建议,以促进网络平台新型用工模式的规范发展。
二、网络平台的劳动用工形式
(一)网络平台概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无数个网络信息平台兴起。对于“网络信息平台”,黄丽华和陈帆学者是这么定义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信息平台最初建设的目标是信息传达,之后演变成网上销售,最后发展成生产要素相关的网路产品和服务[5]。
现如今,随着信息技术与经济的不断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激发出新的活力。据第4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较2018年底增长2598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1.2%,较2018年底提升1.6个百分点。较2018年底提升0.5个百分点[1]。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6.39亿,较2018年底增长2871万,占网民整体的74.8%[1]。
从数据中可以窥见,网络平台和产业交融的社会经济正在不断飞速发展,并催生了无数发展机遇。而为了适应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互联网与产业密切联系的时代,满足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型用工关系应运而生。即企业依托互联网创建专属该公司的网络平台,或是依托市场上已有的大型网络平台,利用网络平台招聘和管理员工,在网络平台上发布工作任务,员工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任务、提供劳务,这种情况下的员工被称为网约工,如滴滴平台司机、外卖员等,形成网络平台+网约工这一新型用工模式。
(二)网络平台劳动用工形式及其分类
当今社会,市场上的网络平台繁多,呈现出多种不同用工特点。以下根据业务分配形式、报酬分配方式和网约工提供劳动形式三个方面,对网络平台用工形式做出分类。
从业务分配形式来看,网络用工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指派业务型,即平台接收客户消费订单后,指派给特定的网约工,网约工需根据平台指派完成特定工作任务,按时向消费者提供服务。
竞争业务型,即互联网平台接收消费订单后,将信息发布在网约工共享终端,供网约工选择,或由网约工按照承接时间先后、距离远近、工作资质和网约工平台账号等级等标准进行竞单,令竞争优胜者承接消费订单,余者继续等待和挑选平台发放的订单。
混合型,即某互联网平台通过指派和竞争两种方式来发放业务订单。网约工在完成平台指派的业务后,可依据自身情况参与竞单,使自身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从报酬分配方式来看,网络平台用工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平台支付型,即劳动者完成任务后,客户将服务费用支付给互联网平台,平台按约定比例扣除部分费用后,按照两种方式给网约工发放报酬:一是网约工完成一次任务,平台即刻发放;二是约定发放周期,定期发放网约工在该周期内获得的报酬。
客户支付型,即从业者提供服务后,客户将费用直接支付给从业者,从业者在向互联网平台支付部分费用后,将剩余款项留作自身报酬;或者从业者直接将客户支付的费用作为自身报酬,平台从从业者的预付款项中扣除部分费用。
从网约工提供劳动的对象和时间来看,网络平台劳动用工形式大致分成三大类:
一是不固定、非专职的“打零工”形式,具体表现为网约工并不固定向一个或几个网络平台提供劳动,网约工提供劳动的时间呈现零散、不固定的特点,且网约工并不将供职于平台公司所得的报酬视做主要生活来源,只为了充分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
二是专职化的“打零工”形式。这种形式下的网约工亦未固定劳动提供对象。但向平台公司提供劳动是这位网约工的主业,承接网络平台订单所获得的报酬是其主要生活来源。此时,网约工利用网络与平台公司联系,可以选择工作任务和强度,不会像传统劳动关系中在工作的时间和空间方面受到限制,其对平台公司的从属性较弱,但又依靠平台公司支付的报酬为生,对平台公司有较强的经济依赖性。这一类用工形式和劳动提供者的身份,是本文讨论的焦点。
三是专职化、固定化的网络用工形式。此种形态与传统劳动用工形态十分接近,劳动提供者向一家平台公司全职提供劳动,与平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用工手续完善,通过网络平台听从平台公司的指挥和管理,利用承接平台订单来获取劳动报酬,且劳动时间是固定、连续的。
现实中的互联网平台用工形式常同时具备上述三种分类的特点,呈现复杂繁多的形态,以指派业务类平台为例,这一类中既有平台支付型公司,又有客户支付类公司,而指派业务+平台支付型网络平台既招聘零工型网约工,又吸纳专职网约工。数种用工特点的搭配,衍生出无数种用工形式各异的网络平台,可见网络平台用工形式十分灵活。
(三)网络平台劳动用工形式的特点
依托网络平台的新型用工关系,有利于整合海量的分散化社会人力资源,满足市场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多种需要,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劳动关系的特点。
1.用工关系主体发生改变[6]
一方是用人单位,另一方是劳动者,这是我国传统劳动关系的配置。并且在我国,不是所有单位都能招聘员工,不是所有单位都能成为用人单位,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才可以。但对应到网络平台用工模式中,劳动关系的主体就发生了变化。网约工和平台公司是网络平台用工模式中的两个主体。在这种模式中,从业者要接受管理,向平台公司提供劳动并以此获得报酬。
但由于存在平台公司与网络平台运营商并非同一家公司的情况,即平台公司将平台的运营工作外包出去,平台公司只负责数据更新和平台维护,网约工的工作任务并不是平台公司的主营业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平台公司为规避责任而不与网约工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其他形式的合同等情况,难以确定在网络平台用工关系中,网络平台是否能对应传统劳动关系中的“用人单位”,网约工是否能对应传统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
2.企业管理和网约工提供劳动的方式更加灵活
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不可以任意行动,要听指挥,在用人单位规定的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内,完成个人分内的任务,同时要遵守纪律。用人单位需要提供符合标准的劳动保护,以保护劳动者的人身安全。
在网络平台+网约工这一新型用工形式中,有赖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平台公司和网约工无需面对面交谈,也可通过网络平台与网约工联系,从而使得平台公司对网约工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等方面的限制大大降低。而网约工以承接网络平台的消费订单为主要工作任务,每个订单都有不同要求,使得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时间、地点及劳动方式都呈现出灵活性的特征。总的来看,在新型用工形式中,网约工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脱离了用人单位对工作环境、工作任务、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网约工对企业的人身依附性大大弱化。
3.生产资料的自主性增强
生产资料是指劳动力在使用和再生产中所必须的各类条件和环境[7]。传统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就应该提供工作工具和环境。劳动者就需要接受纪律的监督,同时完成分内任务。而在新型用工形式中,劳动条件的提供方不只限于平台公司。很多网约工不仅需要提供劳动,还需要自备生产资料。如滴滴司机需要自备车辆以承接滴滴平台的载客订单;外卖员需要自备交通工具和食物保温箱,以承接外卖平台的食物外送订单。
4.劳动报酬的支付更加复杂
传统就业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会在建立劳动关系时,商定好关于劳动报酬的组成因素、发放时间和发放形式,并将相关内容写入劳动合同。而且劳动报酬往往与劳动者的个人绩效挂钩,劳动者所在单位的整体生产销售业绩对劳动者个人劳动报酬的影响不大。
在新型用工形式下,网约工对照着从网络平台接受的订单要求,付出自己的劳动,以此来得到劳动报酬。但因网约工提供劳动的灵活性,使得网约工在每一自然月提供的劳动量不固定,新型用工关系的报酬支付不再像传统就业中按月定期支付,更多是一次性支付或阶段性支付。
综上所述,在信息时代下,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和不断出现的各类用人需求,使得“网络平台+网约工”这一新型用工模式应运而生,满足当下劳动力市场需求、激发经济新活力的同时,也从多方面颠覆了传统劳动关系。
(四)网络平台用工形式的用工关系争议
网络平台用工形式很复杂,跟传统用工形式很不一样。因为网络平台+网约工模式太过新式,司法人员也不能确定:网络平台能不能承担用人单位的角色。北京朝阳法院2018年发布的《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显示,2015年以来,该院就受理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案件188件。笔者总结发现,在网络平台和网约工之间是否存在用工关系、网络平台是否需要承担用工责任的问题上,法院有以下两种观点:肯定用工说和否认用工说。
1.肯定用工
说即网络平台能视作用人单位,它需要承担责任。否定用工说即网络平台不能当作用人单位,它不需要承担责任。
从案件数量来看,以判决方式结案的105件相关案件中,确认平台与从业者直接建立劳动关系的案件为39件、占比37.1%;认定双方不建立劳动关系的案件为58件、占比55.2%。
肯定用工说首先,以“好厨师”APP平台为例,在张琦与上海乐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案件中,法院认为张琦与乐快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在审判过程中,乐快公司辩称:张琦与乐快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这个协议约好了:张琦和乐快是合作,而不是乐快雇佣张琦。法院则认为,张琦和乐快公司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看的不是所签合同的形式,最主要看双方的“合作”模式。在这个案件中,虽然张琦和乐快公司签订的是《合作协议》,但乐快公司对张琦有严格的劳动管理和规定,要求张琦在指定的工作地点完成指定的工作任务,依照张琦的劳动质量发放劳动报酬、进行奖惩,并按时用银行转账的支付形式向张琦发放报酬。且张琦受公司的纪律监督,需要按要求完成任务,并以此获得劳动报酬。从上述情况来看,张琦在经济上和人格上,对乐快公司都有较强的从属性。因此推导,张琦是乐快公司聘用的劳动者,不是乐快公司的合作人,乐快公司是张琦的用人单位
综上所述,法院认定乐快公司是张琦的用人单位,乐快公司应该担负用工责任,张琦的合法权益应该受到劳动法律法规的保障。
再看“滴滴出行”平台,在尹广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被告冯兴鲁是滴滴出行平台的司机,当时被告开着小客车,而原告就坐在这辆车上,因冯兴鲁驾驶不当而受伤。尹广华因此受到了身体和精神上难以弥补的损伤,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冯兴鲁和滴滴出行公司进行赔偿。
虽然滴滴出行辩称:滴滴出行与冯兴鲁不存在用工关系,滴滴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法院认为,冯兴鲁在发生事故时,他是为了完成从滴滴平台接收的任务,冯兴鲁和滴滴出行签订了用车服务合同,作为滴滴网约车平台的签约司机,冯兴鲁应该完成合同上约定的工作任务。滴滴出行和冯兴鲁存在用工关系,劳动纠纷发生时,滴滴出行需要承担用工责任。
以上两个案件,法院均认为平台公司与网约工之间存在用工关系,平台公司应该承担用工责任。
2.否定用工
说首先以外卖配送平台为例,在周继红与张民、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中,被告张民在配送“蜂鸟配送”订单途中撞伤原告周继红。
根据查清的事实,蜂鸟配送APP本身没有运营任务,它的运营任务外包给被告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而拉扎斯公司与被告天津食锦餐饮服务公司签订蜂鸟配送代理合作协议。食锦餐饮得到授权,得以在天津市内配送蜂鸟产品。因此,法院认为拉扎斯信息公司与天津食锦餐饮服务公司员工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即被告张民与被告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用工关系,张民只与天津食锦餐饮服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被告张民是在向天津食锦餐饮公司提供劳动时受伤的,其在工作出现的事故应由天津食锦餐饮服务公司承担。
其次,以直播平台为例,黄钰雯、广州吉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此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黄钰雯和广州吉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根据查清的事实,原告黄钰雯和被告广州吉大文化传播签订《网络主播独家签约合同》,约定他们是合作关系,更有一条“乙方收益不视为与甲方建立任何劳动关系所得”的约定,且合同中仅就黄钰雯未经许可不得在其他网站做主播做出限制,并没有对黄钰雯在何时、何地、以什么内容工作做要求。除此之外,在合同期间,黄钰雯没有因为长期不直播而被吉大扣工资、评低绩效,吉大公司也没有帮黄钰雯购买社会保险。综合上述情况,法院认为黄钰雯和广州吉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以上两个案件中,法院均认为平台公司不是网约工的用人单位。平台无需承担用工责任。
三、网络平台的劳动关系认定
互联网平台技术与产业经济、劳动力市场的结合使得网络平台用工形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网络平台是否存在用工责任,对于这个问题,司法人员也没有统一意见。
网络平台与网约工之间的法律关系是界定网络平台责任的基础[3]。
要明晰网络平台是否存在用工责任,首先要搞清楚网约工能不能被定义为劳动者,网约工和平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但新型网络用工呈现的形态不同于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这对我国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发起了挑战。
(一)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
了解劳动关系的法律定义,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但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劳动法领域的相关规定并未对劳动关系做出具体界定[8],即《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在法律层面也仅采用判断主体是否为法定的劳动关系主体来界定劳动关系[9]。立法的不完善给司法适用造成一定的困难。
《劳动合同法》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如果劳动关系建立,应该采取了什么措施,或者应达到哪种状态。从《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和第十条可知,判断一个用人单位和一个劳动者之间,是否有劳动关系,要看他们有没有签合同,和实际用工情况。
但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出现了许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没签合同的情况。这种情况,可根据《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来判断双方的劳动关系情况。
综合《通知》和《劳动合同法》,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只能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来确定双方的关系。而在这样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在哪里工作、何时工作、工作至少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在工作场合和工作时间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以用人单位的要求为准。劳动者用提供的劳动,从用人单位处换取工资,这就是“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有较强的人格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的含义。我国以人格从属性作为劳动关系的核心,经济从属性是对人格从属性的具体诠释,组织从属性被包含在人格从属性中[3]。目前,法学界尚未对从属性做出明确的定义,笔者将结合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及理论对三大属性进行简要分析。
1.人格从属性
虽然法律地位平等,但是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较强的人格从属性也被发现和证实。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何时何地工作、怎么工作、工作应该达到什么效果的要求,劳动者都要接受并做到。
如果劳动者没有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用人单位有权根据劳动者的行为采取如增减奖金和报酬、决定晋升或调动等奖惩措施。劳动者在提供劳动时,需要严格按照用人单位关于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任务的要求,提供质量符合要求的劳动,并接受用人单位的监督。
经济从属性按照《通知》的第一条第二、三款: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应是用人单位业务组成的一部分,且劳动者以此获得劳动报酬。从这几条条款,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劳动者承担的工作,是用人单位得到市场占比和利润的主要项目,并且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可以帮助用人单位赚取金钱、扩大市场份额和市场知名度,就可以认为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有经济方面的依赖和从属。除此之外,笔者认为经济从属性还包括:在开展工作之前,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事先约好哪些事件会影响劳动者的工资金额,用人单位什么时候、用什么形式给劳动者发报酬,用人单位应该依法给劳动者买社保等等。
而能够证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存在经济从属性的资料,则是用人单位给付工资的银行流水凭证、社会保险支付凭证等资料,劳动者接收的工作邮件和接收劳动报酬的凭证等。
2.组织从属性
另外,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还有组织从属性,意思就是: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只能在一个用人单位工作,并且该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在哪里工作、用什么工具工作,与哪些人组成工作团队等,劳动者都要遵守。遇到工作困难时,劳动者可以向用人单位请求帮助。工作中,劳动者需要听从用人单位的指挥,依照用人单位的要求,提交合格的工作成果。
以上就是笔者对劳动关系三大属性的简要分析。
(二)网络平台劳动关系的认定困难
在上一部分内容中,笔者已分析了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包含的内容以及三大从属性的含义。而将传统劳动认定标准和网络平台用工模式对比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网络平台劳动用工模式与传统劳动认定标准有许多不相适配之处。然而,如果粗暴地将网络平台劳动用工模式认定为非劳动关系,将其排除在劳动法律法规的保护范围之外,不但会使得网约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还会阻碍“网络平台+网约工”这一新式用工形式和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发展。因此,我们应当结合网络平台用工模式的特点,对比以三大从属性为核心的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分析网络平台劳动关系认定会出现哪些和以往不同的情况,再进一步分析我们需要为明晰、保护和约束网约工和网络平台的关系而采取什么样的做法。
1.劳动关系主体定位模糊[6]
我国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在劳动关系中,一方是用人单位,一方是劳动者。并且不是任何形式的组织,都可以成为用人单位。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这几种组织才可以成为用人单位。但是对于劳动者,在劳动法律法规中,也没有说清楚什么身份的人才可以做劳动者。未知劳动者的认定标准,网约工的法律身份界定就缺乏标准,易引发劳动纠纷。
并且能否将网络平台用工模式中的平台公司对等“用人单位”,也存在争议。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以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建立劳动关系。但在现实中,某些平台公司为了规避用工责任,不会与网约工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签订其他形式的劳动合同。平台公司还认为,它提供的网络平台仅有提供信息和交流空间的作用,并不等同于用人单位。且存在网络平台公司将平台运营
且存在用人单位和网络平台运营商并非同一家的情况,使得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判断平台公司是否等同于传统劳动关系中的“用人单位”。
网络平台用工模式很有灵活性。这样就很难判断,平台公司能不能招聘员工、做用人单位;网约工能不能视为劳动者。用工关系的主体定位模糊,为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认定埋下隐患。
2.人格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变弱
在传统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是领导方,劳动者是被监督的一方。劳动者处于从属地位,需要在用人单位指定的时间、地点、团队中,使用用人单位规定的工作工具来工作。但网络平台用工模式的灵活性较强,即网约工可以依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方便自己工作的时间地点和自己喜欢的内容来提供劳动,再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平台和网约工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网约工不需要时时汇报、事事听训,使得平台公司对网约工的管控力度大大降低。
且网约工可以向多个平台公司提供劳动,不像传统劳动者一般在一定时间内只能与一家用人单位工作。因此,网约工从平台公司的控制中释放出来,人格从属性大大降低。
与此同时,部分平台公司要求网约工自备生产资料,在工作中,网约工也不再依赖平台的管理和帮助,其独立完成劳动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从这一方面来看,网约工对于平台公司的组织从属性降低。
网约工人格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的降低,有利于提高网约工的工作热情及其工作效益。但面对严格以人格从属性为认定核心的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网约工容易被排除在劳动者范围之外,不受劳动关系法律法规的保护。
3.劳动报酬的属性和支付方式复杂
在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承接的工作任务是用人单位的主营业务,用人单位需要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并定期以固定形式支付劳动报酬。但在网络平台用工模式中,平台并不直接参与经营线下的业务,它的主营业务在运营维护、开发软件等方面。平台的主营业务与网约工从事的劳动服务的性质有明显的区别。
网络平台用工模式的报酬给付方式与以往有所不同,并非是用人单位评估劳动者的劳动质量后以银行转账等形式付出劳动报酬,而是大致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在网约工提供劳动后,消费者将服务费用支付给平台,平台按照约定或平台规则划扣一定费用后,再转账到网约工的平台账户上;二是在网约工提供劳动后,消费者将服务费用直接支付给网约工,网约工从中抽取部分以支付平台的相关费用。
虽然网约工的工作任务性质和劳动报酬给付形式不与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严格契合,但对于部分以承接网络平台订单所获得的报酬作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网约工来说,他们对于平台经济还存在较强的经济依赖,需要获得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网络平台用工模式的劳动关系认定对于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模式的挑战在于:依托互联网技术而发展的网络平台用工模式十分灵活,网约工的三大从属性减弱,但并非完全失去劳动关系的特点。而现行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十分严格,只有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可以:有较强的人身、经济和组织从属性。“一刀切”的判断方式无法顾及网络平台用工模式这一新式的用工关系,这可能导致相当一部分的网约工被排除在劳动法律法规的保护范畴之外。
四、网络平台劳动关系认定的建议
“网络平台+网约工”的新型用工模式,利用信息技术促使多种经济产业迸发新的活力,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使得网约工能充分利用其劳动力以提高自身经济收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水平的提高提供一大助力。在此情况下,完善我国劳动法律法规,将网络平台用工模式纳入法律调整和监督范围之下就十分重要。笔者将结合各类资料,为完善我国劳动法律、推动确定网络平台劳动关系和用工责任做出建议。
首先,需要在法律层面明确劳动关系和劳动者的定义。劳动关系和劳动者没有被明确定义,使得司法界对此有许多不同的解读,进而引发争议。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我国现有的各类劳动用工形式和社会经济规范发展的需求,在法律上明确劳动关系和劳动者的定义。
其次,应设置多元化的认定标准。当前,我国的劳动用工领域是传统劳动关系和多种新型劳动关系并存[7],若对所有的劳动关系都用统一标准,则缺乏科学性和灵活性。为了更好地保护不同劳动关系下的劳动提供者,我们可以在充分了解网络平台用工模式后,挖掘出网络平台用工模式与现有的全日制劳动关系、非全日制劳动关系或劳务派遣关系等传统劳动关系的相近之处,并且从规范网络平台+网约工用工模式发展的角度,对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进行适当的增改删减和内容调整,设置每种用工模式都应遵循的一般标准和可视情况而定的弹性条款,不再严格地依靠从属性为唯一判定标准。可建立以从属性为核心、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程度等为综合考虑因素的灵活认定模式。立法有滞后性,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实际生活中定会新情况。而弹性条款的加入,就能使得法律更有包容性,法官能更好地进行司法工作。
并在司法过程中,不局限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的合同和协议,不以协议性质为唯一认定标准,而更多地关注用工实质是否属于劳动关系。以张琦与上海乐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为例,实务中,一些平台公司出于减轻运营成本的考虑,而通过提前签订格式条款的方式排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有意规避雇主责任。所以,劳动法律法规和司法认定标准要充分考虑网络平台用工模式的灵活性,以正确的方式对这一新型用工模式进行调整,从实质上去判别劳动关系的存在。
再者,要同时兼顾网络平台和网约工的公平。在传统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一定要提供工作保护,购买五险一金,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这一模式在传统经济模式中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然而面对劳动对象多重化、专职和零工模式并存的网络平台用工模式,照搬社会保险和最低工资的要求,则会对平台公司造成过重的负担。虽然在短时间内会使网约工的劳动报酬水平上涨,但从长期来看,则不利于平台公司的发展,从而打击了“网络平台+网约工”这一新型用工模式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前进。因此,我们需要在法律层面,结合平台公司对网约工的管控程度和网约工的劳动自主性对二者的权利义务进行科学划分。
除此之外,网络平台企业还需完善自身的制度建设。互联网平台企业应该建立合法合理、全面细致的企业劳动规章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并强化规章制度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多听从网约工的意见,以科学的方法减少运营成本[10],方可预防和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
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对灵活新颖的网络平台用工模式做出及时科学的回应,不仅可以提高网约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平台公司的有序发展,也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增添活力。因此,我们需要在法律层面定义劳动关系和完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在司法层面更注重用工实质,从而科学认定网络平台劳动关系,明晰网约工的法律身份和合法权益,界定平台公司的用工责任,促使“网络平台+网约工”新型用工模式的良好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a).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9-08
[2]郑雯. 论共享经济模式下的用工法律规制[D]. 山东大学, 2019.
[3]刘文科, 郑雯. 网络平台用工责任之类型化探析——以共享经济为背景[J]. 研究生法学, 2018,33(03):17-33.
[4] Clair Brown, BaEiehen green, Miehael Reieh. Labor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黄丽华, 陈帆. “互联网+”背景下劳动用工形式和劳动关系问题的初步思考[J]. 经济研究导刊, 2019(12):119-120.
[6]董斐. “互联网+”背景下非标准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制[D]. 南京工业大学, 2017.
[7]李彦. “互联网+”模式下我国劳动关系认定规则的反思与完善[J]. 法制与社会, 2018(26):53-54+65.
[8]孙秀.“互联网+”平台模式下的劳动关系认定[D]. 华中科技大学, 2019.
[9]王美荣. 论网约工的劳动关系认定及权益保护[D]. 广西师范大学, 2019.
[10]胡珍.“互联网+”背景下劳动争议的处理[D]. 兰州大学, 2019.
1、如文档侵犯商业秘密、侵犯著作权、侵犯人身权等,请点击“文章版权申述”(推荐),也可以打举报电话:18735597641(电话支持时间:9:00-18:30)。
2、网站文档一经付费(服务费),不意味着购买了该文档的版权,仅供个人/单位学习、研究之用,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未经授权,严禁复制、发行、汇编、翻译或者网络传播等,侵权必究。
3、本站所有内容均由合作方或网友投稿,本站不对文档的完整性、权威性及其观点立场正确性做任何保证或承诺!文档内容仅供研究参考,付费前请自行鉴别。如您付费,意味着您自己接受本站规则且自行承担风险,本站不退款、不进行额外附加服务。
原创文章,作者:打字小能手,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447766.cn/chachong/1215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