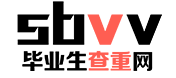中文摘要
目的 基于家庭视角,以系统相互作用模型为理论框架,探讨产妇和配偶二元支持应对、抑郁情绪、亲密关系和社会支持之间的联系,为产妇和其配偶的心理干预提供可靠的依据。
方法本次试验采取横断面研究,以便利抽样法抽取300对自2019年3月至10月期间就诊安徽省某三甲医院产科门诊的产妇及其配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国际上研究成熟的各种量表检测相关指标。具体如下:二元支持应对量表(Dyadic Coping Inventory,DCI)用于检测产妇和配偶的二元支持应对;抑郁情绪的评定我们依赖于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partum Depression Scale,EPDS);对于亲密关系的评估标准我们使用婚姻调适量表(Short Marital Adjustment and Prediction Test,MAT);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用于评价社会支持水平。数据分析过程使用统计软件SPSS19.0和Mplus7.0,对结果进行处理分析主要应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主体-客体效应分析、相关分析和配对t检验等统计学方法。
结果
产妇的产后抑郁水平在年龄、婚龄、职业、文化程度、主要照顾者、与公婆关系、医保、新生儿性别、分娩方式、产次这些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家庭人均月收入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产妇的配偶发生产后抑郁的水平在年龄、从事行业方面、文化程度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产妇产后抑郁平均得分为(10.43±4.72)分,配偶产后抑郁平均得分为(7.44±3.77)分;产妇二元支持应对平均得分为(116.25±16.01)分,配偶二元支持应对平均得分为(118.29±14.90)分;产妇亲密关系平均得分为(86.62±22.21)分,配偶亲密关系平均得分为(98.63±4.21)分;产妇社会支持平均得分为(36.31±5.79)分,配偶社会支持平均得分为(22.65±2.28)分。配对t检验显示,产妇及配偶的压力沟通、相互支持应对、代办支持应对、共同支持应对、消极支持应对、亲密关系、社会支持及产后抑郁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产妇产后抑郁与二元支持应对(r=-0.517,P<0.05)、亲密关系(r=-0.356,P<0.05)、社会支持(r=-0.359,P<0.05)呈负相关。配偶产后抑郁与二元支持应对(r=-0.531,P<0.05)、亲密关系(r=-0.300,P<0.05)、社会支持(r=-0.314,P<0.05)呈负相关。产妇及配偶的亲密关系、二元支持应对、社会支持得分两两相关(r=0.272~0.556,P<0.05)。产妇及配偶各自的亲密关系、社会支持在二元支持应对与产后抑郁间起主体中介作用;产妇亲密关系在配偶二元支持应对与产妇产后抑郁间起客体中介作用;配偶社会支持在配偶二元支持应对与产妇产后抑郁间起客体中介作用。
结论
本研究发现产妇及配偶产后抑郁水平较高;产妇及配偶产后抑郁受到各自二元支持应对的影响,产妇产后抑郁受到配偶二元支持应对的影响;产妇及配偶亲密关系与社会支持在二元支持应对与产后抑郁间起主体-客体中介作用。医护人员在指导产妇积极心理调适时,应重视配偶对产妇的影响,开展以夫妻为中心的产后抑郁的干预研究。
关键词产妇 配偶 二元支持应对 亲密关系 社会支持 产后抑郁
1引言
1.1产妇及配偶产后抑郁
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出生人口数明显增加,2016年和2017年的出生人口数分别为1786万和1723万人,较“十二五”期间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1]。近年来新闻报道中关于孕产妇产后抑郁所致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孕产妇的心理健康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围产期女性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明显要高于其他时期,其中产后抑郁较常见。
Pit于1968年首先提出了产后抑郁症(postpartum depression, PPD)这个病名,它属于神经性抑郁症[2],抑郁、烦躁激动、哭泣等比较多见,也有食欲减退、疲乏或睡眠障碍,甚至伴有幻觉或自杀。产后42天内一般是该病的高发期,轻者产后3至6个月能够自愈,而较重的情况甚至可以持续1至2年。近年来随着该病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其研究工具也在不断变化。关于PPD的发生率,国内外报道的发生率并不完全一致,有研究结果证明这与选择的样本量差异、用于PPD研究的量表工具及设计不一致、国内外关于PPD的诊断标准不同、同一产后妇女的患者评估时间不同其PPD的症状可能不同、患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差异性相关,总之,上述来自方方面面的原因导致国内外文献关于该病的患病率报道不一。国外约有13-19%的女性在孕期及产后有不同程度的产后抑郁症状[3,4]。国内产后抑郁的研究主要是对产后抑郁情绪的研究,其发生率在1.1%-52.1%[5]。
研究表明产妇患有产后抑郁,其配偶也经历着同样甚至更多的焦虑与抑郁[6]。Goodman[7]发现新生儿父亲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在1.2%至25.5%之间,而伴侣患有产后抑郁的新生儿父亲产后抑郁发生率则在24%至50%之间。一项Meta分析结果提示国内产妇配偶的PPD在2007至2015年发生率为13.6%,产后6周产后抑郁的几率最高达28.7%,但发生该病的几率会随着时间下降,如6至8周时是11.4%,8-24周时则降至5.5%[8]。
1.2产后抑郁的影响
产后抑郁通常会产生方方面面的不良后果,一方面对产妇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威胁,由于产妇发生抑郁的病理结果还可以影响夫妻关系,甚至是妊娠结局,可能导致胎儿生长受限、早产、低出生体重儿[9],还能引起婴幼儿认知功能降低,行为发育迟缓或情感障碍[10],患急慢性疾病的几率增高[11],甚至孕产妇会出现自杀以及杀婴等严重行为[12]。
有趣的是,孕产妇一旦发生产后抑郁,对其配偶的影响反而比对产妇自身的影响更为可怕。Escribe-Aguir教授的研究团队[14]和van den Berg等人[13]的实验结果得出了上述结论:一旦产妇发生产后抑郁,孕产妇另一半的也有可能出现抑郁症状,而且这种不良的抑郁症状持续时间比产妇更长,恢复正常更难。甚至,罹患产后抑郁的产妇的配偶很可能由于产后抑郁情绪而表现出暴力倾向,而产妇往往容易受其伤害,最终导致夫妻关系变得紧张。李玉红等观察发现,具有抑郁情绪的父亲与孩子间情感、言语的互动交流较少,对儿童早期的认知、行为和情感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Pinheiro等[15]采取同时评价产妇及配偶PPD的出现状况及对两者进行相关分析的方法,得出产妇和配偶出现产后抑郁呈正相关。
1.3标题自拟(主要从产后抑郁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到引入二元支持应对)
亲密关系是产妇与配偶在共同应对压力时产生的亲密感受。研究表明,亲密关系与产后抑郁呈负相关关系的趋势显著;解释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当孕产妇与配偶之间的亲密关系降低将会直接导致抑郁严重程度不断攀升,亲密关系与抑郁严重程度之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反比关系[16]。婚姻关系与孕产妇及其配偶的PPD发生率密切相关。在亲密关系较低的个体中,产后抑郁出现几率相对较高,婚姻关系的好坏关系到同一家庭单元中的所有人的身心健康,这一体系中的任何不良关系毫无疑问的都会对稳定家庭的关系构成威胁,因此,我们要强调的是,融洽的夫妻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不稳定的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仅是对夫妻双方的威胁,会导致全部家庭成员的痛苦,个体、家庭,甚至社会都有不良效用。
产妇使用某种途径由外界环境获取信息、保护或安慰的过程我们称为社会支持,包括社会支持利用度和主观、客观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常作为缓冲应激和情绪困扰等的中介因素进行研究。很多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产后抑郁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其水平与产后抑郁的发生几率或严重程度呈负相关[17]。
有研究团队针对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与妊娠妇女发生产后抑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项纵向调查研究,实验选择入组与产妇进行密切观察,观察时间持续纵观妊娠晚期、产后第1周和产后4周。实验结果显示,在整个围产期的持续过程中,妊娠妇女的社会支持可以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了变化,妊娠妇女在妊娠晚期和产后4周的关键时刻其感知社会支持评分较产后1周内低[18]。临床医师都知道围产期对于孕产妇和胎儿都是十分关键的时刻。在围产期的社会支持对于产后抑郁的发生更是十分关键,围产期的良好社会支持可以作为抑郁症的重要缓冲因素。实验结果同样给出了给出上述结论的依据,在妊娠晚期获得良好社会支持的妇女,他们发生产前抑郁概率较没有收到良好支持的妇女是明显降低的;同样的情况在,产后4周妇女同样适用,社会支持评分较高他们发生产后抑郁的概率显著降低。分娩作为常见的应激事件,产妇要应对产后激素波动的影响、母亲角色的转变,新生儿父亲也面临育儿责任、财务压力和父亲身份的转换,这种伴侣双方共同面临的压力与挑战被称为二元压力[19]。二元支持应对(dyadic coping)是指伴侣双方在面对压力事件时的共同决策,二元支持应对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人际过程,其中“一方对压力的评估传达给另一方,另一方感知、解释和解码这些信号,并以某种形式的二元支持应对(对压力沟通采取行动或忽略压力沟通)作出反应”[19]。虽然二元支持应对的主要目的是减轻压力和加强婚姻调整,但它也可以促进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
1.3 研究的理论基础
以往关于压力和压力源的研究,一般都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去实施各项研究,并不认为在关于压力和压力源的研究过程中,亲密关系中的成员压力与支持的影响程度,建立亲密关系的人可以是社会的或者家庭中的成员。近年来,有关婚姻本身以及婚姻关系的研究中,压力逐渐成为这种亲密关系研究的研究热点。压力这个词语可以在研究过程中帮助我们很好的理解亲密关系的质量,是我们研究亲密关系稳定性的切入点。目前较为热门的便是基于亲密关系的压力理论模型,压力理论模型的深层含义是压力对产妇和配偶的调适和婚姻满意度是一种持久威胁。Bodenmann提出的系统相互作用模型理论(Systemic Transactional Model,STM),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该实验说明,在亲密关系得双方,对于压力的缓解方式,由伴侣缓解另一半感受到的压力的优势以及在亲密关系中,伴侣是可以意识到另一半会用什么方式处理压力。在亲密关系得双方均暴露在二元压力过程中,简单说来即是压力事件常与亲密关系中的双方都存在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由于本身事件就对双方均可以产生影响,也可能是压力事件首先引起一方的应激然后由于亲密关系中的双方互相影响导致伴侣同样产生效应反应。该理论阐述了一个重要的结果,那就是二元压力三要素。第一,压力事件作用于亲密关系中的双方的方式;第二,压力产生的源头是来自亲密关系中的双方内部或者外部因素;第三,亲密关系中的双方压力应对的先后时间。
该理论中,把亲密关系中的双方设定为A、B两个不同的个体,二者对压力源呈一个循环反应过程。不论是外界或者源自内部的压力在亲密关系中产生,当B察觉A的压力沟通,将进行编码与评估在以支持性二元应对行为反馈给B压力沟通诱发上述过程。二元支持应对功能可重建及维护伴侣彼此幸福,采取缓解压力、增加信任与亲近来调整配偶关系[20]。二元支持应对压力即是该理论的精所在。这种支持包括四种形式:二元应对、共同二元应对、代办型二元应对、消极二元应对。系统交互模型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怀孕作为一个压力事件,当产妇的压力通过沟通被配偶感知,配偶再以支持性二元应对行为反馈给产妇,缓解产妇的抑郁情绪。
1.4 问题提出、研究假设
1.4.1 现有研究的问题
产后抑郁的研究多以个人为中心,忽略了产妇另一半对产后抑郁的影响,缺乏针对配偶与产妇产后抑郁的二元交互研究。针对产妇,配偶对其产后身心调整具有较大的影响,不过两者关系对产妇和配偶身心健康产生干预的机制尚不明确,这正是本次研究的关键所在。
1.4.2 研究假设
(1)产妇及配偶的二元支持应对与自身产后抑郁与配偶产后抑郁之间有影响;
(2)产妇及配偶亲密关系在二元支持应对和产后抑郁的主体效应中起中介作用;
(3)产妇及配偶亲密关系在二元支持应对和产后抑郁的客体效应中起中介作用;
(4)产妇及配偶社会支持在二元支持应对和产后抑郁的主体效应中起中介作用;
(5)产妇及配偶社会支持在二元支持应对和产后抑郁的客体效应中起中介作用;
1.5 研究目的及意义
1.5.1 研究目的:分析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社会支持、亲密关系与产妇产后抑郁之间的关系。构建以二元支持应对为自变量,亲密关系、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产后抑郁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 以分析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对产后抑郁的作用机制。
1.5.2 研究意义:
(1)本研究分析了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社会支持、亲密关系、产后抑郁之间的关系,为后续开展以夫妻为中心的产后抑郁临床护理干预研究,提供了有效理论依据。
(2)本研究分析亲密关系、社会支持在产后抑郁与二元支持应对间的作用机制,为进行产后抑郁干预性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使临床工作者对配偶支持有利于缓解产妇情绪方面引起重视,继续进行以夫妻为观察对象的相关研究,使其关系更加密切,提高他们的社会支持,减少心理问题而改善生活质量。
1.6 操作性定义
(1)产后抑郁:以抑郁状态、心情沮丧、容易激动,应付能力逐渐下降为主要特点,重者抑郁患者可以出现幻觉或自杀等症状,本质是精神障碍疾病。
随着围产期的定义不断完善,产后抑郁被重新定义为围产期抑郁症(根据2016X《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围产期抑郁症:情绪异常出现的时间为妇女在怀孕期间以及分娩后四周。主要是对产后抑郁情绪的研究,采用EPDS评估孕产妇产后抑郁情绪,以10分作为产后抑郁情绪的临界值[2]。
(2)二元支持应对(Dyadic Coping):二元支持应对是指发生在亲密关系的伴侣之间,夫妻共同对各方压力事件或双方共同压力事件的处理[21]。
(3)亲密关系(Intimacy Relationship):个体之间形成的一种较为持久的亲和关系[22]。
(4)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援来自家庭、亲属、朋友、党团等个人或组织[23]。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19年3月至2019年10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合肥市某三甲医院产科门诊300对产妇及配偶进行调查。纳入标准: 产妇:①年龄大于18周岁;②精神正常,具有一定理解表达能力,能够配合者;③无严重妊娠合并症、分娩并发症;④新生儿健康无并发症。配偶:①精神正常,具有一定理解表达能力;②知情同意能够配合者。排除标准:产妇:①既往有严重精神病史者;②怀孕期间,属于高危妊娠;③孕期发现有重大疾病者;④经研究者解释后拒绝合作者。配偶:经研究者解释后拒绝合作者。
2.2 样本量
根据研究变量影响因素确定样本量的大小。研究变量5-10倍的关系确定样本量。我们的实验研究共21个自变量,含16个变量和产后抑郁、社会支持、亲密关系等5个社会心理变量,所以样本量应在210以上,考虑样本缺失控制在20%的样子,故本实验的研究总样本量暂定为约需产妇和配偶各263例。
2.3 研究工具
2.3.1 入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入组患者的一般情况调查有研究者自行设计完成,内容包括研究对象年龄、学历的情况、工作的情况、家庭人均月收入的情况、住房的情况、婆媳关系、与父母的关系等人口社会学资料及孕产史、分娩方式、新生儿性别等产科资料。
2.3.2 二元支持应对量表(Dyadic Coping Inventory,DCI)
DCI由Bodenmann等人[24]首次用来评估亲密关系的一方在压力中感知的压力沟通和二元支持应对的质量。2008年首次应用的时候,该量表包括压力沟通,积极二元支持应对和消极二元支持应对的3个维度。发展到2016年的时候二元支持应对量表已经有37个条目,5级评分。该量表的发展离不开Xu教授的努力。文献指出[25],实验通过474对中国夫妻中进行跨文化调适,分数越高表示支持行为越多,消极支持应对的条目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支持性行为越多。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9,本研究中该量表产妇与配偶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91、0.86。
2.3.3 婚姻调适量表(Short Marital Adjustment and Prediction Test,MAT)
采用中文版洛克-华莱氏婚姻调适量表[26],此问卷用于评定婚姻幸福程度。问卷共15个条目,问卷总分为各条目得分之和,总分范围为2~158分,得分越高婚姻调适越好,得分<100分者为婚姻失调,≥100分为婚姻调适良好。问卷有良好的信效度,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6。本研究中该量表产妇与配偶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7和0.70。
2.3.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由肖水源[27]编制。该量表共10个条目,分为三个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用以评价受试者的社会支持水平。其中,主观支持指人民可以通过感受到的日常社会生活中被理解尊重及支持的情感体验以及满意度;客观支持指受试者得到的支持来自亲属、朋友或者社会组织。受试者使用他人给与的支持和帮助的程度即为支持利用度。14~74分是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总分范围,分值与获得社会支持度呈正比。量表信效度良好,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4。我们的实验研究中该量表中Cronbach’s α系数在产妇与配偶的分别为0.79、0.72。
2.3.5 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partum Depression Scale,EPDS)
该量表由Cox[28]等于1987年编成,是自评量表,目前在评定产妇是否抑郁和抑郁程度方面最为常用。EPDS共10个条目,心境、乐趣、自责、焦虑、恐惧、失眠、应付能力、悲伤、哭泣和自伤。每个条目分四级评分(0~3分),总分在0~30分。9/10分分值是中文版EPDS作为筛查产后抑郁的最佳临界值,分值越高提示抑郁程度越重,本研究中EPDS≥10表示有产后抑郁情绪[29]。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79,该量表在本次研究中产妇和配偶的Cronbach’s α系数对应为0.83及0.70。
2.4 资料收集
采取直接问卷调查方法,在产后42天产妇进行产后检查时收集资料,向产妇及其配偶说明调查的目的、内容,征得其同意后,下发问卷。如若配偶没有陪同,给配偶发放问卷电子版,或将配偶问卷带回家填写。力求产妇及其配偶独立填写。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31份,收回有效问卷计300份,有效率达93.67%。
2.5 统计方法
对数据进行双录入使用Epidata3.0软件完成,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以SPSS19.0软件完成,采用Mplus7.0进行路径分析。以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统计描述:对于样本中一般人口学资料、二元支持应对量表等量表中各变量作统计学分析,服从正态分布的变量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反之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表示,计数资料使用率和构成比表示。 统计分析:分别计算产妇和配偶二元支持应对和产妇亲密关系等变量的得分,考察产妇和配偶以上变量得分是否存在差异性用配对t检验;使用Pearson分析了解产妇及配偶各自的亲密关系、社会支持等变量的相关性;使用线性回归考察产妇及配偶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最后,使用线性混合模型建立主体-客体互倚模型[30],同时了解主体效应(自变量对自身因变量的影响)和客体效应(自变量对伴侣因变量的影响),进一步了解产妇社会支持、亲密关系与产后抑郁的关系。2.6 质量控制本课题是质量控制贯穿整个研究过程:课题设计阶段、课题实施阶段、资料录入、分析阶段。
(1)处于课题设计阶段的质量控制:①大量阅读国内外文献,通过邮件等方式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确保本实验课题的科学性及可行性;②关于成熟评价量表的选择,量表需要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测量变量必须保证真实可靠;③不断征询各方面建议,使课题可以不断完善;④预调查的开展可以进一步完善课题研究。
(2)处于课题实施阶段的质量控制:①医院护理部和相关科室的同意在实验开始前取得;②由研究者本人亲自发放问卷,并在发放问卷过程中与患者取得良好合作关系,患者如有疑问,给与适当解释;③对调查问卷进行登记与编码以便日后核对,需要做到不重不漏,保证调查问卷结果的的真实性和完整性;④召开课题组的工作汇报以及实验中并总结到的问题,以便于及时做出调整和修改。
(3)处于资料录入、分析阶段的质量控制:①采用双人双录入的形式录入问卷数据,并使用Epidata3.1软件给与电子人工智能核对;②由设置专门的质量控制人员,对已完成的调查表每天都要进行反复的检查与核对,发现问题及时修正。
2.7 道德伦理考量
本研究充分保护受试者的权利,我们遵从自愿、有益无害的实验原则,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后再调查,保密原则严格遵守,保证绝不泄露患者隐私和相关信息。本研究方案经安徽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3 结果
3.1 产妇及其配偶的一般资料和临床资料
本研究产妇年龄22-42岁,平均年龄(30.96±3.34)岁;配偶年龄24-43,平均年龄(30.84±3.18)岁,婚龄平均(4.61±1.99)年,产后天数 平均(51.42±4.92)天。产妇和配偶的年龄、文化程度、婚龄、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主要照顾者、与公婆关系、分娩方式和产次等详细内容见表1。
表1产妇和配偶不同人口学和临床资料(n,%)
Tab 1Different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data of maternity and spouse(n,%)


注:“—”代表配偶与产妇的信息相同或无此项信息。
3.2 不同人口学及临床资料的产妇及配偶产后抑郁水平比较
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检验结果显示(表2),人口社会学中的年龄、婚龄、职业、文化程度、主要照顾者、与公婆关系等,及临床信息均与产妇及配偶产后抑郁无显著相关(P>0.05),家庭人均月收入与产妇产后抑郁显著相关(P<0.05)。
表2 产妇和配偶产后抑郁在不同人口学和临床资料的差异(F/t,P)
Tab 2Differences between maternal and spouse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different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data(F/t,P)
| 项目产妇产后抑郁 F/t P 配偶产后抑郁 F/t P
|
| 年龄(岁) 0.152 0.283
18~24 7.35±1.03 1.352 7.25±0.270.445 25~34 10.03±0.96 1.046 ≥45 7.64±0.83 0.742 职业 0.845 医疗卫生行业 8.84±1.26 0.8677.37±0.38 2.733 非医疗卫生行业 10.63±1.652.7449.74±0.47 1.974 文化程度 0.491 初中及以下 9.00±1.001.643 9.39±0.73 0.927 高中或中专 8.85±0.952.635 7.74±0.7 1.737 专科 9.64±0.581.7468.74±0.431.052 本科及以上 8.37±1.742.475 7.73±0.84 0.362 家庭人均收入(元/月) 0.044 <3000 10.05±1.12 0.372 3000~4999 9.64±0.751.463 ≥5000 7.37±0.940.872 主要照顾者 1.456 配偶 8.26±0.740.633 公婆 10.74±0.461.754 父母 8.84±1.051.749 月嫂 8.27±1.030.823 其他 7.84±0.371.837 与公婆关系 0.746 融洽 9.38±0.481.483 一般 9.39±0.730.927 不融洽 10.03±0.261.943 医保 0.344 城镇/职工 7.84±0.72 0.736 新农合 8.94±1.041.948 费用自理 9.74±0.891.735 新生儿性别 0.265 男 10.34±0.83 0.637 女 9.74±1.041.964 分娩方式 0.174 顺产 9.64±0.640.632 剖宫产 9.28±0.381.854 产次 0.297 初产 10.01±0.82 1.295 经产 9.87 ±0.83 1.046 |
3.3 产妇及配偶的二元支持应对、亲密关系及产后抑郁的特点
由表3可知,产妇压力沟通得分均值(26.65±4.65)分,配偶压力沟通均值(35.76±5.71)分,产妇和配偶压力沟通由经配对t检验得出存在显著差异性(P=0.000)的结论,配偶高于产妇;产妇相互二元支持应对得分均值是(33.77±5.43)分,配偶相互二元支持应对均值是(26.02±5.44)分,产妇和配偶相互二元支持应存在显著差异性(P=0.000),产妇的二元支持应明显高于配偶;消极二元支持应对得分均值:产妇得分均值是(25.64±3.98)分,配偶消极支持二元应对均值是(25.25±5.19)分,配对t检验提示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302);代办二元支持应对产妇和配偶的得分均值分别是(12.85±8.41)分、(12.85±8.41)分,经配对t检验得出产妇和配偶代办二元支持应对不存在显著差异性(P=0.108)。产妇共同二元支持应对得分均值是(17.35±3.88)分,配偶共同二元支持应对均值是(34.32±5.12)分,配对t检验得出产妇和配偶共同二元支持应对存在显著差异性(P=0.0000);二元支持应对总分均值产妇和配偶分别是(116.25±16.01)分、(118.29±14.90)分,配对t检验得出产妇和配偶二元支持应对总分存在显著差异性的结论(P=0.000),产妇产后抑郁得分均值是(10.43±4.72)分,配偶产后抑郁均值是(7.44±3.77)分,由经配对t检验得出产妇和配偶产后抑郁存在显著差异性(P=0.000),产妇产后抑郁得分显著高于配偶。产妇亲密关系得分均值是(86.62±22.21)分,配偶亲密关系均值是(98.63±4.21)分,产妇和配偶亲密关系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选择配对t检验),产妇亲密关系得分显著高于配偶。
表3 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亲密关系、社会支持与产后抑郁得分及差异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scor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aternal and spouse dual support coping, intimacy, social support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 产妇 配偶 t P |
| 压力沟通26.65±4.65 35.76±5.71 -2.41 0.000
相互支持应对33.77±5.43 26.02±5.44 -3.13 0.000 代办支持应对8.41±4.50 12.85±8.41 4.95 0.108 共同支持应对17.35±3.88 34.32±5.12 -4.73 0.000 消极支持应对25.64±3.98 25.25±5.19 1.033 0.302 总二元支持应对 116.25±16.01 118.29±14.90 -1.61 0.000 亲密关系86.62±22.21 98.63±4.21 4.42 0.000 社会支持 36.31±5.79 22.65±2.28 6.87 0.000 产后抑郁10.43±4.72 7.44±3.77 -2.08 0.000 |
3.4 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亲密关系、社会支持及产后抑郁的相关性分析
将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得分、二元支持应对各维度得分、亲密关系得分、社会支持得分与产后抑郁得分进行Person相关分析。产妇产后抑郁与二元支持应对(r=-0.517,P<0.05)、亲密关系(r=-0.356,P<0.05)、社会支持(r=-0.359,P<0.05)
呈负相关关系。配偶产后抑郁与二元支持应对(r=-0.531,P<0.05)、亲密关系(r=-0.300,P<0.05)、社会支持(r=-0.314,P<0.05)呈负相关关系。产妇产后抑郁与配偶产后抑郁呈正相关(r=0.380,P<0.05)。二元支持应对、亲密关系、社会支持得分两两相关(r=0.272~0.556,P<0.05)。详见表4。
表4 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亲密关系、社会支持及产后抑郁的相关性分析
Tab 4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aternal and spouse’s dual support coping, intimacy, social support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 产妇 | 配偶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 产妇 | 1.二元应对 | 1 | |||||||||||||||||
| 2.压力沟通 | .715** | 1 | |||||||||||||||||
| 3.相互支持应对 | .883** | .466** | 1 | ||||||||||||||||
| 4.代办支持应对 | .745** | .386** | .667** | 1 | |||||||||||||||
| 5.消极支持应对 | .862** | .482** | .770** | .667** | 1 | ||||||||||||||
| 6.共同支持应对 | .676** | .361** | .473** | .359** | .453** | 1 | |||||||||||||
| 7.社会支持 | .556** | .396** | .470** | .515** | .477** | .346** | 1 | ||||||||||||
| 8.亲密关系 | .512** | .330** | .471** | .472** | .475** | .272** | .403** | 1 | |||||||||||
| 9.产后抑郁 | -.517** | -.395** | -.401** | -.396** | .434** | -.402** | -.359** | -.356** | 1 | ||||||||||
| 配偶 | 1.二元应对 | -.088 | -.044 | -.044 | -.107 | -.080 | -.097 | -.060 | -.135* | .125* | 1 | ||||||||
| 2.压力沟通 | -.041 | -.054 | -.028 | -.079 | -.038 | .023 | -.050 | -.118* | .059 | .466** | 1 | ||||||||
| 3.相互支持应对 | .039 | .028 | .030 | .020 | .054 | .018 | .023 | -.067 | .016 | .438** | .326** | 1 | |||||||
| 4.代办支持应对 | .045 | .027 | .014 | .085 | .036 | .042 | .026 | .067 | -.060 | -.529** | -.412** | -.469** | 1 | ||||||
| 5.消极支持应对 | -.078 | -.060 | -.038 | -.150** | -.067 | -.034 | -.055 | -.178** | .056 | .626** | .191** | .222** | -.294** | 1 | |||||
| 6.共同支持应对 | -.064 | -.004 | -.014 | -.096 | -.073 | -.102 | -.068 | -.074 | .124* | .859** | .425** | .378** | -.433** | .328** | 1 | ||||
| 7.社会支持 | -.052 | -.033 | -.028 | -.054 | -.049 | -.052 | -.024 | -.080 | .098 | .747** | .375** | .367** | -.386** | .302** | .650** | 1 | |||
| 8.亲密关系 | -.088 | -.068 | -.054 | -.104 | -.058 | -.080 | -.096 | -.103 | .134* | .842** | .466** | .407** | -.463** | .340** | .768** | .657** | 1 | ||
| 9.产后抑郁 | -.023 | .009 | -.025 | .061 | -.030 | -.078 | .051 | -.024 | .380* | -.531** | -.252** | -.235** | -.346** | .088 | -.332** | .314** | .300** | 1 | |
注*:P<0.05,**P<0.001
3.5 产妇及配偶产后抑郁的单因素回归分析
以产妇及配偶产后抑郁作为因变量,分别将二元支持应对、亲密关系和社会支持作为独立预测因素纳入回归方程,进行单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产妇的二元支持应对(β=-0.122,P<0.05)、亲密关系(β=-0.023,P<0.05)、社会支持(β=-0.069,P<0.05)能负向预测其产后抑郁情绪。配偶的二元支持应对(β=-0.101,P<0.05)、亲密关系(β=-0.048,P<0.05)、社会支持(β=-0.134,P<0.05)能负向预测其产后抑郁情绪。
表 5产妇及配偶产后抑郁的单因素回归分析
Tab5 Un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 for maternal and spouses
| 产妇产后抑郁配偶产后抑郁
变量 β S.E t P变量 β S.E t P |
| 产妇 配偶
家庭人均月收入-0.174 0.033 -0.044 P<0.05 家庭人均月收入-0.093 0.022 -0.063 P<0.05 二元支持应对 -0.122 0.019 -6.470 P<0.05 二元支持应对 -0.101 0.017 -0.169 P<0.05 亲密关系 -0.023 0.012 -1.896 P<0.05 亲密关系 -0.048 0.009 -5.169 P<0.05 社会支持 -0.069 0.049 -1.408 P<0.05 社会支持 -0.134 0.042 -3.126 P<0.05 |
注:β表示标准化回归系数;S.E表示标准误。
3.6 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与产后抑郁的主体-客体互倚模型分析
以产妇和配偶的二元支持应对作为预测变量,产妇和配偶的产后抑郁作为结果变量构建主客体互倚模型。在图1中,图中横线为主体效应,代表产妇自身以及配偶的二元支持应对对产妇产后抑郁的影响;交叉线代表客体效应,包括产妇的二元支持应对对配偶产后抑郁的影响和配偶的二元支持应对对产妇产后抑郁的影响两方面。依据本研究构建的主客体互倚模型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产妇的产后抑郁同时受产妇自身(B=-1.285,P=0.002)和配偶(B=-2.007,P=0.000)二元支持应对的影响;(2)配偶的产后抑郁仅仅受自身二元支持应对的影响(B=-0.974,P=0.000),与产妇二元支持应对不存在统计学意义(B=0.297,P=0.836)。

图1产妇和配偶的二元支持应对及产后抑郁的主体和客体效应
Fig1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ffects of dual support for maternal and spouse coping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3.7产妇和配偶的二元支持应对、亲密关系与产后抑郁的主体-客体互倚中介模型分析
为了考察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亲密关系与产后抑郁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图3-5的基础上加入了亲密关系进行模型估计。模型适配数据良好,c2=0.462,P=0.000,CIF=1.000,SRMSR=0.113,RMSEA=0.164。结果显示,主体效应显著,产妇二元支持应对可以影响自身产后抑郁,此影响通过自身亲密关系实现。配偶二元支持应对通过自身亲密关系影响自身产后抑郁;配偶二元支持应对通过产妇亲密关系影响产妇产后抑郁,客体效应显著,详见图2。

注:虚线表示不显著路径,实线表示显著路径,同下
图2 产妇和配偶二元支持应对、亲密关系与产后抑郁的主体-客体互倚中介模型
Fig 2Subject-object intermediation model for maternal and spouse dyadic coping, intimacy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3.8 产妇和配偶的二元支持应对、社会支持与产后抑郁的主体-客体互倚中介模型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社会支持与产后抑郁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图3-5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支持进行模型估计。模型适配数据良好
c2=0.012,P=0.000,CIF=1.000,SRMSR=0.033,RMSEA=0.000。结果显示,主体效应显著,产妇二元支持应对可以影响自身产后抑郁,此影响通过自身社会支持实现。而配偶的二元支持应对通过自身亲密关系影响自身产后抑郁;配偶二元支持应对通过产妇亲密关系影响产妇产后抑郁,客体效应显著,详见图3。

图3 产妇和配偶二元支持应对、社会支持与产后抑郁的主体-客体互倚中介模型
Fig 3The subject-object intermediation model of maternity and spouse dual support coping, social support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4 讨论
4.1 产妇及配偶产后抑郁水平
研究[31]已证实EPDS不仅可对女性进行围产期抑郁筛查,也同样适用于男性。本研究纳入300对产妇及配偶,以EPDS评分≥10分作为评定产后抑郁的临界值,产妇产后抑郁的平均得分为10.43±4.72,产后抑郁发病率为45.1%,与以往研究中1.1%-52.1%的产后抑郁发生率一致[5]。配偶产后抑郁的平均得分为7.44±3.77,产后抑郁发生率为31.4%,高于以往研究中2.5%-25.0%的产后抑郁发生率[7]。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高于配偶,与Yin-Ping Zhang[32]等研究结果一致。
新生儿的到来对于产妇和配偶的生活与心理而言皆是重大改变,分娩造成身体的创伤,身体形象的改变,繁重的育儿任务而导致的疲劳与睡眠紊乱,家庭照顾中心的转变,育儿知识和技能的缺乏等可能增加产妇产后出现焦虑、抑郁情绪的概率。研究表明[33]不良生活事件、经济状况以及缺乏产前信息和分娩教育是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角色,责任,沟通,亲密感,共同价值观以及婴儿出生后获得支持的变化会导致夫妻关系不和,可能会加重产妇配偶抑郁症状,而产妇配偶的抑郁情绪会影响夫妻有效沟通,导致压力增加和关系冲突。产妇及配偶需要度过充满压力的角色适应期。
研究表明[34]产妇产后抑郁是配偶产后抑郁的预测因素,在患有产后抑郁的家庭中,其配偶出现产后抑郁的风险也会相应增加。与有抑郁情绪的家庭成员一起xxxx对人际关系、工作、教育、社交生活、以及身心健康产生影响。夫妻同时患有产后抑郁会增加家庭压力影响夫妻关系,婚姻幸福感下降。产妇可通过传统的“坐月子”调整饮食、恢复体力、调节情绪,而男性的情绪易被忽略,受传统文化影响,男性倾向于掩饰自己的情感来适应社会和家庭角色。
4.2 产妇与配偶亲密关系与产后抑郁的相关性
本研究显示,产妇亲密关系水平低于配偶。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变化,女性既要承担经济支出,又要承担家庭分工中主要职责,压力增加。研究发现[35],我国民众婚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总体表现为男性高于女性。家庭收入水平与婚姻满意度也存在着密切关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婚姻满意度也在提升。产妇亲密关系水平低于配偶可能与女性在婚姻中期望获得更多情感支持有关,而现实与期望产生的差距以及婚姻中对配偶过多要求造成产妇对婚姻不满意。
本研究表明亲密关系与产后抑郁两因素为负相关(P<0.001),与Mobarakabadi A[36]等结果相同,婚姻满意度同产后抑郁呈显著负性相关,若满意度下降,便会加重抑郁。产妇在分娩后1个月身体尚未彻底恢复,处于情感脆弱期,还需照看新生儿,家庭成员尤其配偶的支持是她们主要的的社会支持。因此配偶应当主动分担新生儿的照顾工作,比如换尿布、哄睡、起夜拍嗝等。还应关心产妇的心理需求,在产妇情绪不佳时,配偶应及时予以言语或行动方面的支持,缓解产妇情绪,防止其困于育儿烦恼中,对生活失去兴趣。
4.3 产妇与配偶社会支持与产后抑郁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产妇社会支持水平高于配偶社会支持水平。在我国,产褥期除了丈夫以外还有父母、亲友协助照顾产妇、整理家务、照顾婴儿以及为她们提供直接的物质帮助等。与男性相比,女性能够从更多的渠道(例如朋友、其他家庭成员等)获得支持并且通过这些渠道释放一些压力。产妇产褥期主要是由配偶看护,但是配偶除了需要看护产妇,另外还需要工作以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由于二者相冲突,使得配偶没有充裕时间进行社交活动,因此获得的社会支持渠道减少,加重了配偶的压力。此外还与男性性格有关,中国男性奉行坚强独立的人格意识,在面对困难时即使能够获得他人帮助,却常认为靠自己就能解决问题而拒绝别人的帮助。社会支持对产后抑郁有利,两者程度之间呈反比[37]。
社会、家庭或医护人员的支持对产妇尤为重要,含物质、情感、评价和信息等方面,这些支持使产妇更快地进入母亲角色,接受并正确地看待自己,降低产妇因不能适应角色变换而出现负面情绪及产后忧郁,避免产后抑郁。为了帮助产妇配偶在家庭里担任好“父亲”和“丈夫”角色,我们应针对在产褥期的产妇配偶也进行科学的指导。
4.4 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与产后抑郁的主体-客体效应
二元支持应对是指两人共同对其中一方压力事件或双方的压力事件的处理,这发生在有亲密关系的伴侣之间。[38]。压力沟通是指彼此表达自己的消极情绪,通常也作为一种积极二元应对方法。相互支持应对指伴侣间通过某种方式(语言或非语言)向帮助对方的应对努力,例如向对方表示共情理解、表达诚心、提出意见等。代办支持应对指伴侣之中一方为了减轻对方的压力,将另一方责任及任务完全承担起来。消极支持应对是指回应表现为表浅的、敌对的、矛盾的,存在距离感、不真诚、不感兴趣或不乐意提供帮助。共同支持应对即夫妻或伴侣之间都同样重视压力,应对过程中投入对等,如一起放松、联合寻找信息和互相帮助共同解决问题等。
研究表明配偶的二元支持应对高于产妇的二元支持应对,与Stephanie Alves[39]等研究结果一致,与没有抑郁症状的产妇相比,抑郁症状严重的产妇较少与他人沟通压力,患有抑郁情绪的女性更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可能与产妇忙于照顾新生儿,导致产妇产生耗竭感使得自身应对效能减弱。产妇与配偶的二元支持应对无差别(P=0.108),与Bodenmann[21]等的研究一致,其指出男性传达的压力越多,伴侣参与沟通、解决压力的能力越强。
产妇及配偶的二元支持应对对个体自身的产后抑郁存在主体效应。产妇及配偶在面对产褥期各种生理心理问题时,能做到积极沟通,共情理解,互相帮助共同解决问题,相互支持应对方式能够给予伴侣帮助与支持,这不仅能提高自我效能感与自尊,还能提高自身情绪的积极性。
本研究表明,配偶的二元支持应对对产妇产后抑郁有客体效应,而产妇的二元支持应对不影响配偶的产后抑郁,与前期结果相同,有研究显示女性在产褥期遇到问题时会对伴侣的依赖性增加,而伴侣的支持行为能减轻产妇负担,使产妇感受到被保护和被珍惜从而减少抑郁情绪。但中国男性大多不善于表达,医务人员可通过提高配偶的倾听、沟通技巧,在沟通中保持良好的态度,更加关爱呵护妻子。
4.5 亲密关系在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与产后抑郁间的主体-客体互倚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产妇和配偶彼此的亲密关系在二元支持应对与产后抑郁间起中介作用,为主体中介作用;产妇亲密关系在配偶二元支持应对与产妇产后抑郁间起中介作用,为客体中介作用。二元支持应对正向预测亲密关系,亲密关系负向预测产后抑郁,即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水平越高,其亲密关系水平越高,产后抑郁水平越低。
社会交换理论中互惠性原则指出积极的二元支持应对对个体的心理状况有益[40],伴侣一方发出的行为会引发伴侣另一方的回应,并且回应在伴侣间形成循环。通过向伴侣沟通、倾诉压力可以了解自己真正的感受,伴侣接收传达的信息并作出应对,反馈给个体。产妇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尤其在情感上的支持)来源是其配偶,社会认知加工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等都指出个人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寻求帮助的资源是婚姻。
在应对压力事件时,产妇和配偶如果能够做到在遇到问题时能够互相提建议、相互帮助、共情理解,那么伴侣双方的亲密感受都会大大提高,从而改善抑郁情绪。这提示研究人员在制定改善产妇及配偶产后抑郁的干预究中不能孤立的只关注个体,而是要整合患者和配偶来进行,积极开展以夫妻为中心的干预。
4.6 社会支持在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与产后抑郁间的主体-客体互倚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产妇及配偶各自的社会支持在二元支持应对与产后抑郁间起中介作用,为主体中介作用;配偶社会支持在配偶二元支持应对与产妇产后抑郁间起中介作用,为客体中介作用。二元支持应对正向预测社会支持,社会支持负向预测产后抑郁,即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水平越高,其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产后抑郁水平越低。
研究显示,社会支持是积极二元应对与关系满意度的中介变量,热情外向、积极乐观、善于交际的个体能与家庭成员有效沟通,情感关系密切,更易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能帮助孕产妇有效的克服孕产期遇到的各种生理和心理问题,明显的弥补家庭支持不足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帮助产妇获得一定的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有效降低产妇产后不良心理情绪的出现。社会支持的缺乏尤其是来自配偶的支持缺乏会增加产后抑郁的患病风险。积极应对水平高的产妇及配偶获得更高水平的社会支持,有效避免或改善抑郁情绪。社会支持的来源不但包括伴侣、亲友及其自身家庭,医护人员也在不同产妇的产后社会支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医生可以在产妇“坐月子”期间到其家中进行随访,指导产妇科学“坐月子”及正确哺乳、抚育新生儿。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系统交互模型理论探讨了产妇与配偶二元支持应对、亲密关系、社会支持与产后抑郁的关系。研究发现产妇及配偶产后抑郁水平较高;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亲密关系与社会支持能负向预测产后抑郁;产妇及配偶产后抑郁受到各自二元支持应对的影响,产妇产后抑郁受到配偶二元支持应对的影响;产妇及配偶亲密关系与社会支持在二元支持应对与产后抑郁间起主体-客体中介作用。
6 研究的创新之处
(1)本研究立足于家庭环境中的夫妻关系层面,以系统交互模型为理论框架,探讨了产妇及配偶二元支持应对、亲密关系、社会支持与产后抑郁的关系,丰富了产后抑郁的相关理论。
(2)以产妇及配偶为研究调查对象,分析两者相互支持应对与产后抑郁相互作用与影响,凸显配偶作为产妇非专业性社会支持资源的临床意义,可以为今后以夫妻为中心的产后抑郁干预提供依据。
7 研究的局限性与展望
(1)受限于时间、场所等,取样范围较局限,样本代表性难以保证,使结论的推广存在局限性。
(2)随着产后产妇身体恢复与新生儿照护需求的变化,产后抑郁和二元支持应对也会出现变化,另外未动态描绘二元支持应对对产后抑郁影响的变化轨迹,后期可采用纵向研究进一步描述。
参考文献
[1]李希如.2017年我国“全面两孩”政策效果继续显现[EB/OL].http://www. stats. gov.cn/tjsj/sjjd/201801/t20180120_1575796.html,2018-01-20/2018-08-16.
[2] Pitt B.Atypical depression following childbirth. Br J Psychiatry, 1968, 114(516): 1325.
[3] O’Hara M.W, McCabe J. E.Postpartum depression: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13,9:379-407.
[4] Banti S, Mauri M, Oppo A, Borri C, Rambelli C, Ramacciotti D, et al. From the third month of pregnancy to 1year postpartum. Prevalence, incidence, recurrence, and new onset of depression. Results from the prenatal depression-research & screening unit study[J]. Compr Psychiatry,2011,52(4):343-351.
[5] 钱耀荣.晏晓颖.中国产后抑郁发生率的系统分析[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3.29(12):1-3.
[6]Field, T., Diego, M., Hernandez-Reif, M., Figueiredo, B., Deeds, O., Contogeorgos, J., & Ascencio, A.. Prenatal paternal depression.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2006,29, 579-583.
[7]Goodman, J.H., 2004b. Postpartum depression beyond the early postpartum period.Journal of Obstetric, Gynecologic, and Neonatal Nursing: JOGNN 33, 410-420.
[8]王婷婷,徐阳,李战战,陈立章.中国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及其与产妇产后抑郁关系的Meta分析[J].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16,41(10):1082-1089.
[9] Bettina,Hausner H,Wittmann M.Recognizing and Treating Postpartum Depression[J].Dtsch Arztebl Int,2012,109(24):419-24.
[10] Hamid Mirhosseini, Seyed Ahmad Moosavipoor, Mohammad Ali Nazari,et al.Cognitive Behavioral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Following Maternal Postpartum Depression: A Review Article[J].Electronic Physician,2015,7(8):1673-1679.
[11] Abdollahi, Rezai Abhari, Zarghami.Post-Partum Depression Effect on Child Health and Development[J]. Acta Med Iran. 2017,55(2):109-114.
[12] Yim IS, Stapleton LRT, Guardino CM, Hahn-Holbrook J, Schetter CD.Biological and psychosocial predictors of postpartum depression:systematic review and call for integration[J].Annu Rev Clin Psychol.2015,11: 99-137.
[13] van den Berg MP, van der Ende J, Crijnen AA, et al. P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pregnancy are related to excessive infant crying[ J]. Pediatrics, 2009, 124(1): e96-e103.
[14] Escribe-Aguir V, Gonzalez-Galarzo MC, Barona-Vilar C, et al. Factors related to depression during pregnancy: are there gender differences[ J]. 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 2008, 62(5): 410-414.
[15] Pinheiro RT, Magalhães PVS, Horta BL, et al. Is paternal postpartum depression associated with maternal postpartum depression?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 Brazil[ J]. Acta Psychiatr Scand, 2006, 113(3): 230-232.
[16]Mobarkabadi A,Fallahchai R,Askari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Weman who Visited Health Centersin Bandar Abbas city [J].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1999,24(1):69-84.
[17]陈莉莉.婴儿气质、产妇感知压力对产后抑郁的影响及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研究[D].山东大学,2018.
[18]Li Y,Long Z,Cao D,et al.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cross the perinatal period:A longitudinal study[J].Joural of Clinical Nursing,2017.
[19]Bodenmann G. A systemic-transactional view of stress and coping in couples[J]. Swiss J Psychol,1995,54:34-49.
[20]Bodenmann G, Randall AK. Common factors in the enhancement of dyadic coping[J]. Behav Ther, 2012, 43(1):88-98.
[21]Bodenmann, G. Dyadic cop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marital functioning[J].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11,32:27-31.
[22]钟年,程爱丽.社会文化变迁与中国人的亲密关系[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4(11):97-102.
[23]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 : 88-100.
[24]Timmerman GM.A concept analysis of intimacy[J].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1991 ,(12):19-30.
[25]Xu F, Hilpert P, Randall AK, et al. Validation of the Dyadic Coping Inventory with Chinese couples: Factorial structur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and construct validity [J]. Psychol Assess, 2016, 28(8):e127-140.
[26]Tim W,Regan A,Sylvie D,et al.Cross-sec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dyadic coping and anxiety,depression,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for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 and their spouses[J].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2014, (96):120–127.
[27]肖水源,杨德森.社会支持对身也健康的影响[J].中国也理卫生杂志,1987(1):184-187.
[28]Cox J L,Holden J M,Sagovsky R.Detection of postnatal depression,Development of the 10-item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J].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1987,150(6): 782-786.
[29]马秀华,宋风丽,康淑玲,等.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在产后抑郁症筛查中的应用[J].中国医刊,2017,52(2):52-57.
[30]李育辉,黄飞.成对数据分析之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APIM)[J].心理科学进展, 2010,(08):1321-1328.
[31]Matthey S,Barnett B,Kavanagh DJ,et al. Validation of the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for men and comparison of item endorsement with their partners[J].J Affect Disorders,2001,64(2/3):175-184.
[32]Yin-Ping Zhang,Lu-Lu Zhang,Huan-Huan Wei,et al.Post partum depression and the psychosocial predictors in first-time fathers from northwestern China[J]. Midwifery,2016,35.
[33]Demontigny,F.,Girard,M.E., Lacharite,C.,et al.Psychosoc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aternal postnatal depression[J].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2013,42(150)44-49.
[34]Ramchandani P,Stein A,Evans J,et al.Paternal depression in the postnatalperiod and child development: a prospective population study[J]. Lancet,2005,365(9478) :2201-2205.
[35]王俊秀,陈满琪.社会心态蓝皮书[M].第8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369.
[36]Mobarakabadi A,Fallahchai R,Askari M.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in Women who Visited Health Centers in Bandar Abbas city[J].J.Appl.Environ,2014,23(14).358-377.
[37]何瑛,何国平.430例产妇产后抑郁发生及相关因素的研究[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1,17(13):1539-1541.
[38]Falconier MK, Jackson JB, Hilpert P, et al. Dyadic coping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 meta-analysis [J]. Clin Psychol Rev,2015, 42(6): 28-46.
[39]Stephanie Alves , Ana Fonseca , Maria Cristina Canavarro, et al.Dyadic coping and dyadic adjustment in couples with women with high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pregnancy [J].Journal of Reproductive and Infant Psychology,2018,8(11)64-68.
[40]张耀方,方晓义.城市新婚夫妻求助表达、伴侣支持应对和婚姻满意度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19(4):496-498.
1、如文档侵犯商业秘密、侵犯著作权、侵犯人身权等,请点击“文章版权申述”(推荐),也可以打举报电话:18735597641(电话支持时间:9:00-18:30)。
2、网站文档一经付费(服务费),不意味着购买了该文档的版权,仅供个人/单位学习、研究之用,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未经授权,严禁复制、发行、汇编、翻译或者网络传播等,侵权必究。
3、本站所有内容均由合作方或网友投稿,本站不对文档的完整性、权威性及其观点立场正确性做任何保证或承诺!文档内容仅供研究参考,付费前请自行鉴别。如您付费,意味着您自己接受本站规则且自行承担风险,本站不退款、不进行额外附加服务。
原创文章,作者:1158,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447766.cn/chachong/1374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