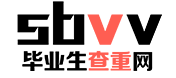中文摘要
目的:
观察全反式维甲酸(all-trans retinoic acidATRA)联合亚砷酸(arsenic trioxide ATO)诱导分化治疗初诊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c APL)的临床疗效;研究APL患者在上述药物诱导分化治疗期间的肝脏毒性;分析影响APL患者肝脏毒性的危险因素以及肝功能损伤对预后的影响;同时对临床上骨髓细胞形态学符合APL的PML/RARa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进行临床分析,探讨其临床特征、治疗方案及预后,以期为以后APL患者临床诊疗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方法:
1、收集整理2012年06月0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60例初诊APL患者临床资料,按诱导分化治疗后肝功能情况分为肝损害组和非肝损害组。(1)分析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BMI(体质质量指数)、白细胞计数、预后危险分组、治疗方案、预防性保肝治疗、感染、分化综合征、完全缓解率、完全缓解时间等方面的差异,对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采用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寻找APL患者在诱导分化治疗期间肝损害发生的危险因素,以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2)将60例APL患者分为单药诱导分化治疗组和双药诱导分化治疗组,使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并对各组生存较进行Log-rank双侧检验。分析两组患者在完全缓解率、OS率、复发率等差异,以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3)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并对各组生存曲线比较进行Log-rank检验,分析肝损害对APL患者预后影响,以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收集整理2012年06月0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0例形态学符合APL的PML/RARa 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并与同期收治的30例骨髓细胞形态学与分子生物学一致的非APL的AML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分析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方案、预后等方面的差异。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平均数±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表示,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和Fisher精确检验;以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在此次纳入的60例初诊诱导分化治疗前肝功能正常的APL患者中,肝损害发生率为73.33%,其中轻度肝损害发生率为31.81%,中度肝损害率为50%,重度肝损害发生率为18.18%。对肝损害进行单因素分析发现性别、体质质量指数(BMI)、白细胞计数、诱导分化治疗方案、预后危险分组、分化综合征(DS)的发生对肝损害有影响(p<0.05)。对单因素阳性指标进行多因素分析,发现白细胞升高、诱导化疗方案、DS是APL患者诱导分化治疗期间肝损害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2、通过对20例形态学符合APL的 PML/RARa 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与30例骨髓细胞形态学与分子生物学一致的非APL的AML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比分析发现,两组患者在以出血起病、诱导分化治疗期间出血、骨髓早幼粒细胞比例、PT、APTT、FIB、产生融合基因、染色体异常、完全缓解率、达CR时间、复发率、首次复发时间、死亡率等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患者在年龄分布、性别、以感染起病、阳性体征、诱导分化治疗期间并发感染及消化道症状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1、ATRA联合ATO在APL的诱导分化治疗中完全缓解率高、复发率及死亡率低,值得在临床中推广;APL诱导分化治疗时发生肝损害率为73.3%,肝损害以轻中度肝损害为主,且肝损害呈可逆性。女性患者、BMI偏高的APL患者在诱导分化治疗中更易发生肝损害。分化综合征、双诱导治疗方案、初诊时白细胞升高是APL患者诱导分化治疗期间发生肝损害发生的危险因素。2、形态学符合APL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具有较高早期出血风险;形态学符合APL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预后较非APL的AML患者差;形态学符合APL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对ATO及ATRA治疗不敏感,需结合基因及染色体核型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
关键词: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维甲酸;亚砷酸;肝损害;PML/RARa基因阴性
第一部分60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诱导分化治疗肝损害分析
1、引言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是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中的一种特殊亚型,即英、法、美(France America British FAB)分型中的M3型,是一种具有独特的临床表现、细胞形态学、分子生物学和细胞遗传学表现的可治愈性疾患[1]。发病年龄多见于20-50岁的中青年。有流行病学研究证实[2],APL的发病率为0.32/10万,在初发的AML患者中占10%-25%[3]。因严重感染、急性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所致的早期死亡率达40%以上,曾被认为是AML中恶性程度最高、致死率最高、预后最差、临床过程最凶险的类型。后随着全反式维甲酸(all-trans retinoic acid ATRA)、亚砷酸(arsenic trioxide ATO)及蒽环类等药物的应用后,使其完全缓解率达到90%以上,治愈率达80%以上[4] ,成为目前治疗效果最好,预后最佳的急性髓系白血病。
约95%的APL患者具有典型的15号和17号染色体异位,即15号染色体上的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基因(promyelocytic leukemia PML)与17号染色体上的维A酸受体α(retinoic acid receptorα RARα)发生断裂、交互异位,形成PML/RARα融合基因,编码PML/RARα融合蛋白。在正常人体内,PML融合蛋白目前已知的共功能特性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1)在生理条件下,协助PML的相关蛋白的定位;(2)阻滞细胞周期抑制细胞生长;(3)活化激活蛋白(Activator protein,AP-1)、肿瘤抑制蛋白p53、转录因子GATA2等表现出转录调控活性;(4)通过Fas和caspas依赖的凋亡途径及非caspas依赖的凋亡途径诱导细胞凋亡。PML/RARα融合蛋白可以使骨髓内原始细胞分化过程被阻滞于早幼粒细胞阶段,从而阻断了粒细胞的正常分化进程,导致大量异常的早幼粒细胞堆积在骨髓中,进而致APL的发生与发展[5]。另外,仍有5%的APL患者不具有典型的PML/RARα融合基因,其主要为PML/RARα的变异体,目前被人们熟知的变异体主要为RARα基因的伙伴基有关,而RARα的伙伴基因有PLZF、Nu MA、NPM、STAT5b、FIP1L1、OBFC2、TBLR、BCOR、GTF2[5-7]等。虽然这些变异体的发生率远远低于PML/RARα融合基因,但其致病机制截然不同,且有研究表明这部分患者大多数对ATRA及ATO治疗不敏感,易复发,死亡率高,总体预后差[8]。
在20世纪60年代前,APL的诱导治疗仅为使用6-巯基嘌呤或联合使用类固醇激素、甲氨蝶呤或甲基乙醛酰肼等,其早期完全缓解 ( complete remission CR)率低,仅为5%-14%,且患者生存时间仅为3-16周(平均为3.5周),多数在2月内死亡或复发[9]。蒽环类药物的使用是APL治疗史的第一个突破,使APL的CR率明显升高。Drapkin等[10]对24例APL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DNR和阿糖胞苷(cytarabine,Ara-C)联合化疗的CR率明显高于其他化疗药物(9/17vs 1/7)。西南肿瘤协作组[11]则通过对不同剂量的DNR疗效观察发现,在诱导过程中DNR剂量的增加与CR率提高及生存期的延长相关,且随蒽环类剂量的增加早期病死率下降,但随之而来的便是耐药性的增高,于是启发人们去寻找更为有效的化疗药物或方法,这为ATRA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Flynn等人[12]通过细胞实验证明了13-顺维甲酸和ATRA均可诱导HL-60 髓样白血病细胞系分化。随后上海瑞金医院医师证明了ATRA诱导培养的白血病细胞分化比13-顺式视黄酸更有效。同时发表了24例APL患者接受ATRA治疗的结果,其中23例获得了CR。2002年北美研究组[13]对单药ATRA与化疗进行比较,认为ATRA单药诱导治疗APL的无病生存(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率及总体生存(Overall survivalOS)率显著优于常规化疗,维持治疗可进一步提高疗效。自此ATRA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而ATRA作为维A酸的衍生物主要通抑制PML/RARα的RARα部分并释放主要转录阻遏物而诱导终末分化,使早幼粒细胞向成熟阶段分化发挥作用。后随着国际上ATRA的广泛使用,目前已经发现该药具有耐药性,且发生耐药的患者再次使用ATRA无效,这些问题均提示了ATRA联合化疗或抗耐药的新药的必要性。于是,20世纪90年代,亚砷酸(arsenic trioxide ATO)首次应用于临床。2010年[14]在中国首先报道三氧化二砷 (ATO)治疗APL患者超过80%完全缓解率(CR) 和分子学缓解率后,研究者设计了多项以ATO作为一线治疗的临床试验,认为无论单用ATO还是联合RTRA,均能获得很高的CR率( ≥ 90%)。亚砷酸[15]主要是能快速降解PML/RARα融合蛋白和野生型PML蛋白,对APL细胞发挥剂量依赖的双重效应,低浓度(约0.6umol/L)诱导细胞分化,高浓度(约2umol/L)诱导细胞凋亡。经过大量的临床试验,ATRA+ATO联合使用能获得较高CR率、较短的达CR时间及低复发率。因此,最终将ATRA+ATO作为现目前初诊APL患者的一线治疗。
化疗是治疗急性白血病的主要手段,但无论是ATRA及ATO,甚至是蒽环类等其他大部分化疗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均能导致肝细胞变形、变性、坏死等,最终导致肝损害,而所致的肝损害多具有无症状、隐匿、可逆转等特点。2013年Petronijevic等人[16]对不同地区的6000多病例分析发现,在引起急性肝衰竭的药物中,化疗药物位居第二位。化疗药物引起的肝损害对急性白血病患者治疗有着重要的影响,轻者影响治疗的顺利进行,而严重者则直接导致肝衰竭、死亡等[4]。2005年Takai等人[17]研究发现,在600例进行联合化疗的急性白血病中,有7.3%的患者发生肝功能损害。2008年甘戈登等人[18]报道了7例患者因ATO致肝衰竭。2014年李福兵等人[19]研究发现在进行联合化疗的146例急性白血病患者中,有11%-40%的患者发生肝功能损害。近些年来,APL的治疗主要使用ATRA及ATO,而ATRA、ATO在为APL患者带来较高的缓解率及生存率的同时,其产生的出血、分化综合征(differentiation syndrome DS)、心脏毒性及肝脏毒性等不良反应仍不容忽视,尤其是在APL诱导分化治疗期间。2006年Mathews等人[20]对不同治疗阶段的ATO与肝脏毒性的发生比例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ATO单剂治疗初诊的APL患者在诱导期、巩固期、维持治疗期的肝损害发生率分别为65.5%、10.3%、20.7%。2011年闫鹤等人[21]报道在初诊的60例APL患者中,使用ATRA及ATO诱导分化治疗中肝损害发生率为73.85%,其中轻度肝损伤占33.33%,中度肝损伤占 50%,重度肝损伤占16.67%。2013年HAO等人[22]通过动物实验研究表明,ATO及ATRA等对肝脏有损害作用。2018年杨槟荧等人[23]研究发现,ATRA、ATO在APL的诱导化疗期间、维持治疗及巩固治疗期间均有肝脏损害,但以诱导化疗期间肝损害更为常见。以上研究及报道均说明ATRA及ATO在APL诱导分化治疗期间易发生肝损害。既然有化疗肝功能损害的存在,这随之又带来保肝药物的预防性使用问题,而目前临床上关于在肿瘤化疗前预防性使用保肝药物问题仍存在争议,2014年zhang等人[24]认为保肝药物在体内含量的高低会影响ATO的治疗效果,认为人体内保肝药物含量高的患者比体内保肝药物含量低的患者更易出现耐药,但发生肝损害的几率又相对内保肝药物含量低的患者低。2015年版国[25]内药物性肝损害诊治指南不推荐预防性使用保肝药物减少化疗药物引起肝损害,另外的一些小样本临床数据分析表明,化疗前预防性使用保肝药物对化疗期间肝损害的发生有效。以上种种研究均表明对APL患者诱导分化治疗期间肝损害分析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及指导价值。
基于以上理论和研究成果,本研究结合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2年06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初诊60例APL患者临床资料,旨在比较APL患者诱导分化治疗及化疗与肝损害的关系,同时分析诱导治疗期间肝损害的特点;分析导致肝功能损伤的影响因素及肝损害对预后的影响。通过对APL患者诱导分化治疗期间肝脏毒性特点的总结和分析,以期为APL的诱导分化治疗期间肝损害的防治提供理论上参考的依据。
2、资料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2.1.1分组
选取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2年06月0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收治的初诊未治的肝功能正常的60例APL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诱导分化治疗后肝功能情况分为肝损害组和非肝损害组,其中肝损害组44例,非肝损害组16例。
2.1.2纳入标准
(1)60例初诊患者均符合2016年WHO推荐的形态学(morphologyM)、免疫学(immunologyI)、细胞遗传学(cytogenetiesC)、分子生物学(molecularM)诊断标准[26];
住院基本资料和临床资料相对完善患者;(3)诱导分化治疗方案均为全反式维甲酸(ATRA)、全反式维甲酸(ATRA)+三氧化二砷(ATO)。
2.1.3排除标准
既往存在肝脏基础疾病,如: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等;诊断明确未进行治疗或未完成诱导分化治疗、依从性较差患者;心肺功能较差患者,如:严重心力衰竭患者、重症肺炎患者等;合并第二肿瘤及妊娠患者;(5)既往存在放化疗病史等患者。
2.1.4随访
APL患者临床资料通过查阅我院电子和纸质档病例资料获得,并且进行随访,随访终止时间为2019 年12月31日。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是指确诊疾病开始至死亡时间或末次随访时间。这段时间的生存率为OS率。
2.2研究方法
2.2.1 研究方法及观察指标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我院2012年06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初诊未治的75例APL患者,其中治疗前既有肝功能损害15例,选取治疗前肝功能正常的初治APL患者60例纳入研究。通过比较诱导分化治疗后肝损害组与非肝损害组的临床特征,找出诱导分化治疗期间肝损害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肝损害对APL患者预后的影响。
患者年龄、性别、入院时间、确诊时间、是否有长期用药史,是否存在基础疾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肥胖、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于初诊时均进行骨髓常规、43种白血病融合基因、流式免疫分型、染色体检查。常规检查指标:血常规、凝血功能、肝功能(主要包括ALT、AST、ALP、GGT、TB)、肾功能(诱导治疗期间,每2天检测上述指标,若血象及凝血异常恢复正常,每周查两次;若肝肾功能出现异常,给予纠正后及时复查。)诱导化疗方案、化疗起止时间及支持治疗,保肝药物使用情况。 (5)治疗过程中重要并发症、胃肠道反应、重要感染及出血等。
2.2.2 APL患者危险分组
根据Sanz[27]预后分层标准将初诊APL患者分为高、中、低危组(具体分组(见表1)。
表2.1 APL危险分组
| 血常规指标 危险分组
低危组 中危组 高危组 |
| WBC(×109/L) <10 <10 >10
PLT(×109/L) >40 <40 – |
注:WBC正常值为(4-10×109/L),PLT正常值为(100-300×109/L)
2.2.3 肝功能损伤分级
我院肝功能正常值标准上限(Upper limit of normal valueUNL):直接胆红素(Direct bilirubin DBL):5.1μmol/L,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L):17.1μmol/L,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transaminase ALT):50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AST):50U/L,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 ALP):150U/L,谷氨酰转肽酶(glutamine transpeptidase GGT):50U/L。肝功能损害分级根据欧洲药物学术会议(2018年版)达成的药物性肝损伤的诊断标准共识[28]进行分级(表2)。
表2.2药物性肝损伤分级
| 肝功能指标 分 级
轻度 中度 重度 |
| DBL 1~2×UNL 2~5×UNL >5×UNL
ALT 1~2×UNL 2~5×UNL >5×UNL AST 1~2×UNL 2~5×UNL >5×UNL ALP 1~2×UNL 2~5×UNL >5×UNL GGT 1~2×UNL 2~5×UNL >5×UNL |
2.2.4 治疗方法
(1)诱导缓解治疗方案
ATRA单药诱导分化治疗:临床疑诊APL患者一旦诊断APL,立即开始ATRA治疗,具体用法:25mg.m-2.d-1,分2次口服,直至血液学完全缓解。
ATRA联合ATO诱导分化治疗:临床疑诊APL患者一旦诊断APL,立即开始ATRA治疗,待流式免疫分型及PML/RARα融合基因检测确诊为APL,立即加用ATO治疗。具体用法为:ATRA 25mg.m-2.d-1,分2次口服,直至血液学完全缓解;ATO 0.16mg.kg-1.d-1,静脉滴注21-28天。
在诱导分化治疗期间,当APL患者出现白细胞升高(>10×109/L)时,加用小剂量阿糖胞苷,具体剂量为100mg.m-2.d-1,当白细胞有下降趋势时停用,一般使用5-7天。
(2)预防性保肝治疗
在诱导分化治疗开始同时进行保肝治疗,一般使用5-7天,具体方案为:还原性谷胱甘肽 1.8g/天,静脉滴注。或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 456mg/天,口服。
(3)肝功损伤的治疗
在发生轻度肝功能损伤时仅予口服保肝药物治疗,在发生中度肝功能损伤时予口服联合静脉进行保肝治疗,而在发生重度肝损伤时,除了予以口服及静脉保肝外,还予减少ATRA及ATO用量的80%,随后及时复查肝功能,如若肝功能未见好转或加重则直接停用ATO,同时使用化疗药物进行保肝治疗,待肝功能恢复后再恢复化疗。保肝药物具体方案:还原性谷胱甘肽 1.8g/天,静脉滴注;门冬氨酸鸟氨酸注射液5g/天,静脉滴注;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 456mg/天,口服等。
2.2.5 疗效标准
(1)完全缓解治疗标准(参考2003年国际协作组AML疗效判定标准[29])
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on CR):①无白血病浸润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工作生活正常或接近正常;②外周血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1.5×109/L,外周血血小板计数>100×109/L,血红蛋白>100g/L(男性)或血红蛋白>90g/L(女性);③外周血白细胞分类中无白血病细胞;④骨髓象中I+II型(原始单核+幼稚单核或原始淋+幼稚淋)<5%。
复发(Relapse):2017版复发难治性髓系白血病诊疗指南将复发定义为CR后外周血重新出现白血病细胞或骨髓原始细胞<0.050(除外其他原因如巩固化疗后骨髓重建等)或髓外出现白血病细胞浸润][30]。
(2)肝损伤疗效标准判定
治愈:①临床症状(如:黄疸、乏力、厌油等)消失;②肝脏酶学改变:ALT<50U/L,AST<40U/L,DBL<5.1umol/L.
好转:①临床症状(如:黄疸、乏力、厌油等)好转;②肝脏酶学改变:ALT、AST、DBL下降但未降至正常;
无效:①临床症状(如:黄疸、乏力、厌油等)无好转;②肝脏酶学改变:ALT、AST、DBL 未下降或上升。
2.3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5.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表示,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并对各组生存曲线比较进行Log-rank检验。P < 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研究结果
3.1 APL患者诱导分化治疗期间肝损害的发生率
在此次纳入的60例诱导分化治疗前肝功能正常的患者中,发生化疗肝损害的患者44例,发生率为73.33%,其中轻度肝损害14例,发生率为32%;中度肝损害22例,发生率为50%;重度肝损害8例,发生率为18%,以轻中度损害为主。

图3.1轻、中、重度肝损害发生率
3.2肝损害影响因素分析
3.2.1初诊APL患者发生肝功能损害的单因素分析
60例初诊APL患者中,男性21例(35%),女性39例(65%),中位年龄41岁(20-67岁)。根据Sanz预后分层标准评分,高危患者14例(23%.33),中危组33例(55%),低危组13例(21.67%)。入院后给予ATRA或ATRA+TAO诱导分化治疗,治疗过程中发生肝损害44例,未发生肝损害16例。将发生肝损害与无肝损害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组患者在年龄、预防性保肝治疗、感染、出血、完全缓解率、达完全缓解时间等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性别、BMI、诱导分化治疗方案、预后危险分组、DS的发生等方面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1)
表3.1两组初诊患者一般资料与疗效比较
| 特征 | 总人数 | 肝损伤组 (n=44) | 非肝损伤组 (n=16) | 统计量 | P值 |
| 年龄(例,%) | 1.431 | 0.232 | |||
| ≤60岁 | 46 (83.33) | 32 (86.36) | 14 (87.50) | ||
| >60岁 | 14 (16.67) | 12 (13.64) | 2 (12.50) | ||
| 性别(例,%) | 8.352 | 0.004 | |||
| 男 | 20(33.33) | 10(22.73) | 10(62.50) | ||
| 女 | 40(66.67) | 34(77.27) | 6(37.50) | ||
| BMI(例,%) | |||||
| <18.5 | 3(5.00) | 2(4.55) | 1(6.25) | 8.377 | 0.015 |
| ≥18.5 &<25 | 7(11.67) | 2(4.55) | 5(31.25) | ||
| ≥25 | 50(83.33) | 40(90.90) | 10(62.50) | ||
| WBC(×109/L)(例,%) | 4.364 | 0.037 | |||
| ≥10 | 50 (83.33) | 34 (77.27) | 16 (100.00) | ||
| <10 | 10 (16.67) | 10 (22.73) | 0 (0.00) | ||
| 预后危险分组(例,%) | 6.790 | 0.034 | |||
| 高危组 | 14 (23.33) | 14 (31.82) | 0 (0.00) | ||
| 中危组 | 33 (55.00) | 21 (47.73) | 12 (75.00) | ||
| 低危组 | 13 (21.67) | 9 (20.45) | 4 (25.00) | ||
| 治疗方案(例,%) | 6.213 | 0.013 | |||
| ATRA | 29 (48.33) | 17 (38.64) | 12 (75..00) | ||
| ATRA+ATO | 31 (51.67) | 27 (61.36) | 4 (25.00) | ||
| 预防性保肝治疗(例,%) | 33 (55.00) | 21 (47.73) | 12 (75.00) | 3.526 | 0.060 |
| 感染(例,%) | 33 (55.00) | 26 (59.09) | 7 (43.75) | 1.116 | 0.291 |
| 分化综合征(例,%) | 7 (11.67) | 7 (15.91) | 0 (0.00) | 4.670 | 0.031 |
| 完全缓解(例,%) | 57 (95.00) | 41 (93.18) | 16 (100.00) | 1.918 | 0.166 |
| 完全缓解时间 | 28.37±4.64 | 28.46±4.78 | 28.13±4.78 | 0.245 | 0.870 |
3.2.2肝损害影响多因素分析
将上述单因素分析结果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性别、预后危险分组、白细胞计数、治疗方案、分化综合征)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多因素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中白细胞升高、双诱导分化治疗、发生DS的患者在诱导分化治疗发生肝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2
表3.2APL患者诱导分化治疗期间肝损害高危因素分析
| 因素 | 多因素分析 | ||
| OR | 95%CI | P值 | |
| WBC | |||
| 升高 | 1.00 | ||
| 非白细胞升高 | 7.01 | 1.33-36.83 | 0.021 |
| 预后危险分组 | |||
| 低危组 | 1.00 | ||
| 中高危组 | 1.67 | 0.37-7.46 | 0.501 |
| 治疗方案 | |||
| ATRA | 1.00 | ||
| ATRA+ATO | 23.10 | 1.99-264.95 | 0.022 |
| 性别 | |||
| 男 | 1.00 | ||
| 女 | 0.46 | 0.11-1.91 | 0.287 |
| 分化综合征 | |||
| 否 | 1.00 | ||
| 是 | 4.45 | 1.14-19.18 | 0.044 |
3.3治疗与转归
60例初诊的APL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发生肝损害44例,轻中度肝损害予还原型谷光甘肽、多烯磷脂酰胆碱、腺苷蛋氨酸等保肝降酶等治疗,重度肝损害患者除给予上述保肝治疗外,还予诱导治疗药物减量治疗。经过上述方式处理后,29例患者肝功能痊愈,痊愈率达66%,15例患者肝功能好转,好转率34%。未出现因肝损害中断诱导分化治疗甚至死亡等情况。
 图3.2肝损害患者治疗后转归
图3.2肝损害患者治疗后转归
3.5 复发与生存分析
3.5.1APL患者诱导治疗疗效及预后分析
3.5.1.1双药诱导组和单药诱导组诱导治疗期间疗效比较
接受双药诱导和单药治疗患者中完全缓解率分别为100%(31/31)和93.1%(27/29)(p=0.22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接受双药诱导和单药治疗患者中完全缓解时间中位数分别为28天(20-42天)和35(25-51)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双诱导治疗疗效较单药治疗更佳。
3.5.1.2双药诱导组和单药诱导组远期疗效比较
随访时间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60例接受诱导治疗的APL患者,无失访患者,60例患者均进入生存分析,中位随访时间是3.3 (0.13-7)年。接受双药诱导治疗患者中1例复发,29例接受ATRA单药诱导治疗的APL患者中6例复发,诱导组和单药诱导组总复发率分别为3.2%和20.7%(p=0.03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双诱导治疗后APL患者复发率低。随访发现4例患者死亡,均为复发后死亡。其中,31例接受ATRA+ATO双药诱导治疗的APL患者中,复发死亡1人,而29例单药治疗后复发死亡3人。双药组和单药组OS率分别为89.7%和96.8%(p=0.269),预计5年生存率分别为96.0%和90%(见图3.3),单药治疗与双药治疗APL患者的长期预后无差异。

图3.3单药组和双药组患者生存分析
3.5.2肝功能损害对预后的影响
在60例初诊APL患者接受诱导治疗中,肝功能损害的发生率为73.3%(44/60)。肝功能损害者中2人发生死亡,OS率为95.5%(42/44),复发率为(2.3%);16例非肝功能损害者中2人发生死亡,OS率达87.5%(14/16),复发率为0%,两组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96) (图4),两组复发率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292),根据我们的观察可知肝损害对APL患者预后无影响。

图3.4肝损害患者与非肝损害患者生存分析
4、讨论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是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中特殊的亚型,占AML的3.3%~21.2%[30],是一种有较高早期死亡率医疗急症,在不治疗的情况下,中位生存期不到一个月,曾被认为是恶性程度最高、死亡率最高的血液系统疾病,然而通过现代化治疗,即随着全反式维甲酸(ATRA)、三氧化二砷(ATO)的运用使APL成为可治愈的急性白血病。APL的治疗与其他类型不同,包括若干阶段(诱导缓解治疗、巩固治疗、维持治疗等),总体而言,其治疗可能历时1-2年。而现目前APL的诱导分化治疗方案主要以双诱导(ATRA联合ATO)为主,完全缓解率达90%,预计5年生存率达84%-95%[30-34]。
在本研究中,我们回顾性分析了我院2012年06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APL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了ATRA联合ATO、单用ATRA两种治疗方案的临床疗效,研究结果显示,接受双药诱导和单药治疗患者中完全缓解率分别为100%(31/31)和93.1%(27/2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29),这与国内报道相似[35-36]。但双药诱导达CR的时间明显比单药短[双药诱导和单药治疗患者中完全缓解时间中位数分别为28天(20-42天)和35(25-51)天,p<0.05],本研究中,ATRA联合ATO的CR率与国外报道相似,但达CR的中位时间短于国外,2019年欧洲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诊疗指南[37]指出,双药诱导治疗APL达CR升高时间大多数为35天,这考虑跟国内临床工作者一旦骨髓形态学怀疑APL便立即口服ATRA治疗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APL的进展。关于单药组与双诱导组在总体OS率、5年生存率、复发率等问题,本研究中,两组患者OS率分别为89.7%和96.8%(p=0.269),预计5年生存率分别为96.0%和90%。这与既往国内报道相似[38-39],但双诱导治疗的患者复发率低于单药治疗患者。以上均证实了双诱导治疗较单药治疗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诱导分化治疗中疗效更限制,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ATRA治疗APL的主要不良反应有高白细胞综合征、粘膜干燥、头晕头痛、消化道反应、骨关节疼痛、肝损害[40]等。据文献报道,单用 ATRA治疗APL时出现肝功能损害的比例约为12%-30%[41]。ATO在治疗过程中的主要不良反应为分化综合征、骨髓抑制、消化道反应、肝功能异常[42-43]等,有研究表明,单用ATO治疗 APL 时肝损害发生率为 63.6%[44]。通过以上,我们可知ATRA及ATO均具有肝脏毒性,均能导致肝损害的发生。据报道,ATRA联合ATO诱导分化治疗APL肝损害发生率为60%-80%[45],以轻中度肝损害为主。而在本研究中我们对60例初治肝功能正常的APL患者进行分析,其中肝损害发生率为73.33%,轻度肝损害发生率为32%,中度肝损害率为50%,重度肝损害发生率为18%,未出现因肝功能损害导致延误诱导治疗,甚至甚至发生死亡等情况。这与既往报道相符。目前有关于急性白血病诱导化疗期间肝损害相关危险因素研究,如:2009年岳兰竹等人研究性别、年龄、感染、化疗方案与肝损害的关系,发现感染是肝损害的危险因素[46]。2017年李亚娜等人[47]研究性别、化疗阶段、临床危险度、甲氨蝶呤基因、化疗后相关并发症(血红蛋白水平、白蛋白水平、感染)与肝损害的关系,发现肝损害与化疗阶段、血红蛋白水平、白蛋白、感染等因素相关,而贫血、白蛋白<35g/L、感染是化疗后肝损害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目前关于APL诱导分化治疗期间肝损害的危险因素分析研究甚少,且观点不一,2010年郝良纯等[48]研究三氧化二砷的肝脏毒性研究表明APL诱导分化治疗期间肝脏毒性与患者年龄、性别、DIC、发病病程无关,与分化综合征、ATO的剂量相关;2011年闫鹤等[21]则认为男性较女性更容易发生肝损害,年龄>60岁、就诊时白细胞升高是APL诱导分化治疗期间肝损害的危险因素;2018年杨荧兵等人[23]研究认为白细胞升高、分化综合征的发生、化疗方案是肝损害的危险因素,而肝损害的发生与性别、年龄、ATO的蓄积无关。虽然关于APL诱导分化治疗期间肝损害相关危险因素观点不一,但以上研究均表明化疗方案、分化综合征及白细胞升高是APL诱导分化治疗期间肝损害发生的危险因素。本研究根据患者诱导分化治疗后肝功能情况,将60例APL患者分为肝损害组与非肝损害组,通过分析其在年龄、性别、BMI、预后危险分组、白细胞计数、治疗方案、预防性保肝治疗、感染、分化综合征、CR率、CR时间等方面的差异,发现两组患者在性别、BMI、预后危险分组、白细胞计数、治疗方案、分化综合征等方面有差异(p<0.05),而在CR率、CR时间、是否预防性保肝治疗无差异(p>0.05)。
本研究中,年龄在APL患者在诱导分化治疗期间肝损害方面无差异(P>0.05)这与既往朱蕾等人[49]通过研究化疗药物肝损认为老年人存在着肝脏体积变小、代谢酶活性降低以及肝血流量减少,导致药物代谢和消除减慢,可能使患者暴露于较高需要浓度的时间持续较长,最终更容易发生肝损害不相符,考虑一方面这与APL患者发病年龄为中青年相关,另一方面与办研究样本量小、存在分组偏倚等有关。
在本研究中女性较男性更容易发生肝损害。曾有文献报道在ATO诱导分化治疗APL患者时女性较男性更容易发生肝损害[50]。2019年李娜等人[51]在研究152例药物性肝损害分析中也表明女性较男性更易发生肝损害。这可能是女性的药物敏感性较男性高,与女性体内肝微粒体肝药酶的活性低于男性有关。而关于体质指数(BMI)与APL诱导分化治疗肝损害的关系,目前尚不清楚肥胖是否增加肝损害的发生,在本研究中BMI较大者更易发生药物性肝损害,考虑可能与脂肪含量增加,会导致细胞内水分减少,增加了药物的血药浓度峰值,延长其半衰期有关[48]。
对APL诱导分化治疗期间肝损害单因素分析阳性结果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多因素分析,发现分化综合征、双诱导治疗方案、初诊时白细胞升高是APL患者诱导分化治疗期间发生肝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p值分别为0.044、0.022、0.021)。关于分化综合征是APL诱导分化治疗肝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考虑可能均与引起分化综合征的细胞因子风暴机制相关。有研究证实诱导分化的APL细胞,可分泌细胞因子IL-1β、IL-6、IL-8、TNFα[48]最终诱发分化综合征,而这些细胞因子属于炎症因子,又与与肝细胞炎症、免疫反应的发生发展有关,可使肝细胞损伤[49-53],最终导致肝功能损害。IL-1是促炎细胞因子,可促进 IL-6、IL-8、GM-CSF 等释放产生炎症反应。IL-6是促炎因子之一,有研究表明其水平的高低与发生炎症程度相关[49]。IL-6还可激活诱导T、B细胞分化,引起肝脏炎症反应及免疫损伤。此外,IL-6强力诱导急性期反应蛋白,加重肝脏损伤。TNFα作为细胞内的一种促炎细胞因子,研究证实它与肝功能损害严重程度呈正相关[50-52]。一方面TNFα具有的细胞毒性作用能直接损伤肝细胞,另一方面又可以引起肝脏微循环障碍而导致肝细胞死亡,同时,TNFα还可刺激其他细胞因子生长,如 IL-1、IL-8、IFNγ、GM-CSF 等,进一步引起或加重肝损害。因此,在APL患者诱导分化治疗过程中,应密切关注DS的发生,同时应密切监测肝功能,一旦发生分化综合征,应立即使用地塞米松治疗及对症治疗,必要时甚至停用ATRA、ATO,阻止肝损害的发生及进一步恶化。
在本研究中,双药诱导治疗方案是肝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与2018年杨荧兵等人研究报道相似,其引起肝损害考虑一方面与ATRA及ATO本身具有肝毒性相关[54-55],另一方面ATRA与ATO均具有诱导分化APL细胞的作用,分化的APL细胞能产生细胞因子有关,其损伤机制与上述一致。
关于在本研究中初诊时白细胞升高是APL患者诱导分化治疗肝损害的独立危险因素。有文献报道也证实了此观点[56-57],甚至还进一步详细证实了初诊时白细胞>50×109/L患者更易发生肝损害。因此对于高白细胞APL患者,我们应及时采用小剂量化疗药物如羟基脲、阿糖胞苷或高三尖杉酯控制WBC水平,减少大量白细胞被破坏产生的细胞因子对肝脏功能的影响。
另外,本研究中预防性给予保肝治疗与未预防性给予保肝治疗对肝损害的发生无影响(p>0.05),且55%的患者预防性保肝治疗的药物是还原型谷胱甘肽。这与文献报道有所不同,如岳兰竹等人研究发现应用还原性谷胱甘肽预防性保肝治疗可以降低急非淋患者治疗过程中肝损伤的发生[46]。考虑一方面可能与样本量小、分组有偏倚有关,另一方面考虑APL诱导治疗期间肝损伤的发生除与药物因素有关外,还与其他非药物因素相关,如白细胞成倍数升高时常伴随细胞因子释放并介导炎症、免疫损伤有关。还原型谷胱甘肽是体内抗氧化剂,可与毒性反应性代谢产物相结合、清除活性自由基从而发挥保护肝细胞的功能[58],但没有抗炎、调节免疫的作用。如若联合应用具有抗炎、调节免疫功能的保肝药物是否会降低肝损伤的发生,这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虽然,在初诊的APL患者诱导治疗过程中,肝损伤发生率较高,但以轻中度为主,且呈现出可逆转性,及时给予保肝治疗或诱导治疗药物减量等治疗后,肝损伤治疗的有效率达100%,没有因肝脏损伤导致治疗中断使 APL未缓解不良事件发生。
最后,在APL诱导分化治疗过程中,对于初诊时白细胞升高、出现分化综合征的患者,应密切监测肝功能,必要时进行细胞因子检测,密切关注细胞因子与肝损害的相关性。及早给予干预治疗,以期降低肝损伤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保证治疗的顺利进行。
5、结论
(1)ATRA联合ATO在APL的诱导分化治疗中完全缓解率高、复发率及死亡率低,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APL诱导分化治疗时发生肝损害率为73.3%,肝损害以轻中度肝损害为主,且肝损害呈可逆性。女性患者、BMI偏高的APL患者在诱导分化治疗中更易发生肝损害。(4)分化综合征、双诱导治疗方案、初诊时白细胞升高是APL患者诱导分化治疗期间发生肝损害发生的危险因素。
6、研究不足之处
本研究的人数有限,样本量来源单一,仅为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患者;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收集数据主要借助查阅病程记录和检验资料,存在一定的差异性;(3)本研究由于地域及患者文素质水平差异,无法继续对APL患者在巩固治疗期间及维持治疗期间的肝损害进行研究,甚至肝损害与ATO、ATRA蓄积量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陆中纬. 初治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危险因素与预后分析[D].南华大学,2018.
[2]Arthur Zelent, Fabien Guidez, Ari Melnick,等. Translocations of the RARalpha gene in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Oncogene, 2010, 20(49):7186-7203.
[3]María C. Chillón, Marcos González, R García-Sanz,等. Two new 3′ PML Breakpoints in t(15;17)(q22;q21)﹑ositive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Genes Chromosomes Cancer, 2000, 27(1):35-43..
[4]Coombs, CC, Tavakkoli, M, Tallman, M S.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where did we start, where are we now, and the future[J]. Blood Cancer Journal, 5(4):e304..
[5]Siegel RL, Miller KD, Jemal A. Cancer Statistics, 2017. CA Cancer J Clin 2017; 67:7
[6]Chattopadhyay, Anuja, Abecassis, Irina, Redner, Robert L. NPM-RAR binding to TRADD selectively inhibits caspase activation, while allowing activation of NFκB and JNK[J]. Leukemia & Lymphoma, 56(12):1-18.
[7]Goto, Hironori, Kimura, Makoto, Hirano, Naoki,等.NUP98-HOXC13\\r, fusion gene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Pediatric case[J]. Pediatrics International.
[8]Michael B Streiff, Bjorn Holmstrom, Aneel Ashrani,等. Cancer-Associated Venous Thromboembolic Disease, Version 1.2015[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Jnccn, 2015, 13(9):1079-1095.
[9]W G BAKER, N U BANG, R L NACHMAN,等. Hypofibrinogenemic hemorrhage in 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 treated with heparin[J].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964, 61(1):116-123.
[10]Robert L. Drapkin, Timothy S. Gee, Monroe D. Dowling,等. Prophylactic heparin therapy in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Cancer, 41(6):2484-2490.
[11]孙慧. V-TAD治疗50岁以上的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来自X西南肿瘤协作组的研究[J]. 国外医学.输血及血液学分册,1995(06):373.
[12]P J Flynn, W J Miller, D J Weisdorf,等. Retinoic acid treatment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In vitro and in vivo observations[J]. Blood, 1984, 62(6):1211-1217.
[13]Martin S Tallman, Janet W Andersen, Charles A Schiffer,等. All-trans retinoic acid in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Long-term outcome and prognostic factor analysis from the North American Intergroup protocol[J]. Blood, 2002, 100(13):4298-4302.
[14]马向娟, 任汉云, 岑溪南, et al. 化疗、全反式维甲酸联合砷剂序贯治疗成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疗效分析[J]. 中华血液学杂志, 31(5):328-332.
[15]Avvisati G, Lococo F, Paoloni F P, et al. AIDA 0493 protocol for newly diagnosed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very long-term results and role of maintenance.[J]. 2011, 117(18):4716-25.
[16]Bruno, Vincenzi, Grazia, Armento, Mariella, Spalato Ceruso,等. Drug-induced hepatotoxicity in cancerpatients-implication for treatment[J]. Expert Opinion on Drug Safety:14740338.2016.1194824.
[17]Shinji Takai, Hisashi Tsurumi, Kazuki Ando,等. Prevalence of hepatitis B and C virus infection in ha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 and liver injury following chemotherapy[J]. European Journal of Haematology, 2005, 74(2):158-165.
[18]甘戈,孙骏,王佳域,王越. 27例三氧化二砷严重不良反应病例报告分析[J]. 中国药物警戒,2008,05:286-290.
[19]蔣波涛, 李福兵, 廖建生, 等. 药物性肝损害 146 例临床分析[D]. , 2014.
[20]Vikram Mathews, Biju George, Kavitha M Lakshmi,等. Single-agent arsenic trioxide in the treatment of newly diagnosed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Durable remissions with minimal toxicity[J]. Blood, 2006, 107(7):2627-2632.
[21]闫鹤.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诱导治疗期间肝损伤发生率及其相关因素研究[D].吉林大学,2011.
[22]Hao, Liangchun, Zhao, Jishu, Wang, Xiuli,等. Hepatotoxicity From Arsenic Trioxide for Pediatric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J Pediatr Hematol Oncol, 35(2):1.
[23]杨槟荧. 亚砷酸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肝脏毒性的临床研究[D].宁波大学,2018.
[24]Meijuan Sui, Zhuo Zhang, Jin Zhou. Inhibition factors of arsenic trioxide therapeutic effect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2014, 127(19):3503-3506.
[25]Study of Drug Induced Liver Disease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guideline on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J]. 2015, 23(11):810.
[26]Arber, D. A, Orazi, A, Hasserjian, R,等. The 2016 revision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lassification of myeloid neoplasms and acute leukemia[J]. Blood, 127(20):2391-2405.
[27]Miguel A Sanz, Pau Montesinos, Edo Vellenga,等. Risk-adapted treatment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with all-trans retinoic acid and anthracycline monochemotherapy: Long-term outcome of the LPA 99 multicenter study by the PETHEMA Group[J]. Blood, 2008, 112(8):3130-3134..
[28]Qurat-ul-Ain Hafeez, Amna Subhan Butt, Furqaan Ahmed. Manage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B: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Of Physicians In Pakistan[J].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Hepatology, 2018, 8(4).
[29]Cheson B D, Bennett J M, Kopecky K J, et al. Revise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for diagnosis, standardization of response criteria, treatment outcomes, and reporting standards for therapeutic trials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03, 21(24): 4642-4649..
[30]Chillón M C, González M, García‐Sanz R, et al. Two new 3′ PML Breakpoints in t (15; 17)(q22; q21)‐positive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Genes, Chromosomes and Cancer, 2000, 27(1): 35-43.
[31]Lu Y, Li F, Mu Q, et al.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ll-trans retinoic acid plus arsenic trioxide in 177 newly diagnosed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patients].[J]. 2015, 36(5):372-7.
[32] Jaime-Pérez J C, González-Leal X J, Pinzón-Uresti M A, et al. Is There Still a Role for Low-Dose All-Transretinoic Acid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in the Arsenic Trioxide Era?[J]. 2015, 15(12):816-819..
[33]Mahdi Jalili, Marjan Yaghmaie, Mohammad Ahmadvand,等. Prognostic value of RUNX1 mutations in AML: A meta-analysis[J].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Apjcp, 2018, 19(2):325..
[34]Sanz M A, Fenaux P, Tallman M S, et al. Management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updated recommendations from an expert panel of the European LeukemiaNet[J]. Blood, 2019, 133(15): 1630-1643.
[35]陆滢, 李枫林, 牧启田,等. 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砷治疗177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观察[J]. 中华血液学杂志, 2015, 36(5):372-377.
[36] Hu J, Liu Y F, Wu C F, et al. Long-term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ll-trans retinoic acid/arsenic trioxide-based therapy in newly diagnosed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2009, 106(9):3342-3347.
[37]黎民君, 郭丽堃, 陈利媚, et al. 全反式维甲酸、三氧化二砷联合化疗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疗效观察[J]. 医学综述, 2015, 21(2):365-366.
[38]王洁,李叶青,牛兆青. 维甲酸与亚砷酸双诱导结合化疗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临床效果[J]. 中国当代医药,2015,20:133-135.
[39]高丽,王聪蕊,叶娟. 维甲酸与亚砷酸双诱导结合化疗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效果[J]. 航空航天医学杂志,2019,05:575-576.
[40]杨晓刚. 亚砷酸联合维甲酸及化疗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疗效观察[J]. 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19,25:46-48.
[41]Niu C, Yan H, Yu T, et al. Studies on treatment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with arsenic trioxide: remission induction, follow-up, and molecular monitoring in 11 newly diagnosed and 47 relapsed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patients.[J]. 1999, 94(10):3315-3324.
[42]焦力, 王书杰, 庄俊玲, et al. 亚砷酸和全反式维甲酸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疗效和副作用的比较[J].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 2009, 31(5).
[43]XIANG Yang, CHANG Xiao-hui, CHENG Yu-bin. Effect of Post-remission Therapy Mainly with Compound Huangdai Tablet on Long-term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 Western Medicine, 2010, 30(12):1253-1256.
[44]Björnsson E.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Hy’s rule revisited[J]. Clinical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 2006, 79(6):521-528.
[45]C. Kelaidi, S. Chevret, S. De Botton,等. Improved Outcome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With High WBC Counts Over the Last 15 Years: The European APL Group Experience[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7(16).
[46]岳兰竹, 付蓉, 阮二宝, et al. 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肝损伤发生率及其相关因素研究[J].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09(11):1009-1011.
[47]李亚娜.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化疗后肝功能损伤的多因素分析[D]. 青岛大学, 2018.
[48]郝良纯, 赵继顺, 王秀丽, et al. 三氧化二砷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儿的肝脏毒性[J]. 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2011, 26(15).
[49]朱蕾. 过敏体质与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的相关性研究[D].遵义医科大学,2019.
[50]Chalasani N, Fontana RJ, Bonkovsky HL, et al. Causes, clinical features, and outcomes from a prospective study of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Gastroenterology 2008; 135:1924.
[51]Pais, Raluca, Rusu, Elena, Ratziu, Vlad. The Impact of Obesity and Metabolic Syndrome on Chronic Hepatitis B and Drug-Induced Liver Disease[J]. Clinics in Liver Disease, 18(1):165-178.
[52]王可,李慧波,孙丽丽,孔德胜,李英花.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分化综合征的发生机制、早期诊断及治疗研究进展[J]. 医学研究杂志,2019,09:188-191.
[53]Ding, Changhai, Cicuttini, Flavia, Li, Jun,等. Targeting IL-6 in the treatment of inflammatory and autoimmune diseases[J]. Expert Opinion on Investigational Drugs, 18(10):1457-1466.
[54]吕超, 石清兰, 覃倩, 等. 小鼠实验性肝损伤模型的研究进展[J].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2019, 29(1): 107-113.
[55]王涛, 林琴, 刘凤婷, 等. IL-1, TNF-α 在免疫性肝损伤过程中对代谢酶 CYP2E1 的调控作用[J]. 2019.
[56]]高卉. 32例药物性肝损伤患者临床病理特征与细胞因子相关性分析[D].吉林大学,2019.
[57]国当代医药, 2017, 24(8): 34-36.
[58]Zacharias E Suntres. Role of antioxidants in paraquat toxicity[J]. Toxicology, 180(1):65-77.
第二部分:形态学符合APL的PML/RARa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临床分析
引言
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是一组高度异质性血液系统恶性肿瘤,FAB根据骨髓形态学特征将其分为M0-M7型,分别为:M0即急性髓系白血病微分化型;M1即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未分化型;M2即急性粒细胞白血病部分分化型;M3即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又称APL;M4即急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M5即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M6即红白血病;M7即急性巨核细胞白血病。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ML -M3,APL)因t(15;17)异位形成 PML/RARa 融合基因成为AML中特殊的亚型,其对全反式维甲酸(ATRA)、亚砷酸(ATO)靶向药物敏感,是临床公认的一种可治愈的一种急性白血病。
而近年来大部分临床研究一直关注典型的APL患者,对形态学符合APL的PML/RARa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知之甚少。什么是形态学符合APL的PML/RARa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它其实是指一类骨髓细胞形态学支持诊断APL,甚至是流式细胞免疫学也支持APL,但分子遗传学缺乏t(15;17)及PML/RARa 融合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1],经过临床研究,我们发现这类患者,其中一部分诊断为急性早幼粒细胞变异型(hypogranular variant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M3V),目前报道[2-4]的M3v的染色体及基因变异类型主要有累及PML/RARa 变异型和不累及17号染色体的突变型。PML/RARa 变异型既往报道的有t(11;17)(q23;q21)、t(11;17)(q13;q21),即对应的17号染色体上RARa 基因的伙伴基因为 PLZF、Nu MA、NPM、STAT5b、FIP1L1t;不累及 17 号染色体的突变,如 t(11;12)(p15;q13),突变基因为NUP98-HOXC13/11,inv(11)(p15;q22)等。此外,2019年zhang等人报道了1例,既没有典型t(15;17)异位形成 PML/RARa 融合基因,也没有上述基因重排的M3v患者,而是表现为ELL-MLL基因[5]。另一部分则被诊断为非M3型急性髓系白血病。近年来有不少的文献报道此类疾病,2015年的Binal等[1]报道了在48例形态学符合APL的患者中有10例最终确诊为M4,5例确诊为M2。2018年Li等[6]人报道了6例形态学支持APL的AML患者,其中有4例最终确诊为M2,2例为M4,6例患者均有WT1基因的表达。2018年qin等人[7]报道了1例具有CPSF6-RARG基因的AML患者,其形态学类似于APL。2019年peteson[8]报道了1例形态学支持APL的AML患者,最终确诊为M2。此类非M3型AML其大部分存在基因、染色体变异的M2或者M4,极少数为M5[9-10]。
众所周知,典型的APL患者对ATRA及ATO敏感,ATRA联合ATO已成为APL患者的一线诱导分化治疗方案,可使APL患者CR率达90%以上,治愈率达80%,已成为一种可治愈的急性白血病。但对于这类形态学符合APL的PML/RARa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据文献报道其大部分对ATRA及ATO不敏感,2018年tomoo等[11]人报道了5例形态学形态学符合APL的PML/RARa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对ATRA无效。2019年Chen等人[12]报道了5例新型的具有NPM1-RARG-NPM1基因的AML,其骨髓细胞形态学均类似于APL,但均对ATRA及ATO有耐药性。最终此类对ATRA及ATO不敏感患者通过AML常规化疗方案后得到完全缓解,但缓解后容易复发,死亡率高[13]。因此,此类患者的发病机制如何、预后及治疗方案目前尚待进一步研究。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近年来,在临床工作中,我们遇到不少形态学符合APL,但分子遗传学不具有 t(15;17)和PML/RARa 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我们发现其一方面临床特征与APL相似(早期出血风险高),另一方面,大部分患者对ATRA及ATO疗效欠佳,死亡率及复发率高,且预后差。为加强临床工作者对此类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预后及治疗方案的认识,同时为此类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本研究就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2年06月01日-2019年12月31日期间发现的20例形态学符合APL的PML/RARa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同时收集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2年06月01日-2019年12月31日期间收治的30例骨髓与分子生物学检查一致的急性髓系白血病(主要为M2,少数为M4、M5)患者,通过分析探讨形态学符合APL的PML/RARa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临床特征,以期为我院AML的诊疗工作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2、资料和方法
2.1研究对象
2.1.1分组
观察组:选取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2年06月01日-2019 年12月31日血液科收治的形态学符合APL(骨髓形态学特征表现为:骨髓中以颗粒增多的早幼粒细胞为主,占骨髓非红系有核细胞比例≥30%;骨髓中原始细胞比例>20%)的PML/RARa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作为观察组。
对照组:从同期骨髓细胞形态学与分子生物学一致的非M3的AML患者中选取30例作为对照组。
2.1.2纳入标准
1、符合葛均波主编的内科学(第九版)中急性髓系白血病诊断标准;
2、住院基本资料和临床资料相对完善患者;
3、所有患者诱导化疗基础方案分别为:DA(柔红霉素+阿糖胞苷)、HA(高 三 杉 酯 碱+阿糖胞苷)、ATRA+ATO(维甲酸+三氧化二砷)、IA(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
2.1.3排除标准
无法获得准确骨髓细胞形态学、病理报告及分子生物学检查的患者;外院诊断AML,但无我院或其他医院病理科会诊结果的患者;只是门诊就诊而未进行住院治疗的AML患者;诊断明确后放弃化疗的患者。2.1.4随访
AML患者临床资料通过查阅我院电子和纸质档病例资料获得,并且进行随访,随访终止时间为 2019年12月31日。总体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 OS),定义为确诊之日至任何原因的死亡或末次生存随访日;失访病例以末次就诊或随访日期为审视截点。首次复发时间:指APL患者确诊后至第一次复发的时间。
2.2研究方法
2.2.1、收集内容:采用回顾性分析的研究的方法,运用 Exce软件制作关于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2年06月-2019年12月收治的20例APL样AML患者和非M3的AML的临床资料的表格,绘制相关图表,进行描述性分析,同时根据Excel表的内容建立数据库。
2.2.2.观察指标:对符合本次纳入标准的患者,查阅我院病历资料,记录相关临床资料。
2.2.2.1一般情况:姓名、住院号、性别、年龄、电话号码、地址、发病时间、死亡时间。
2.2.2.2临床特征:首发症状、实验室资料、影像学检查;
2.2.3治疗
所有观察组患者均从入院第一天骨髓形态学支持APL后开始口服全反式维甲酸40-60mg/天,分2-3次口服,直至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结果回报,再进一步调整治疗方案为常规化疗方案或双诱导方案;对照组患者从入院后明确诊断及排外化疗禁忌症后立即采用常规化疗方案。常规化疗方案:DA(柔红霉素+阿糖胞苷)方案:柔红霉素60mg,d1-3;阿糖胞苷150mg,d1-5;HA(高 三 杉 酯 碱+阿糖胞苷)方案:高三尖杉酯碱4mg,d1-7;阿糖胞苷,150mg d1-7;IA(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方案:去甲氧柔红霉素6-8mg/天 d1-5,阿糖胞苷150mg/天 d1-5。双诱导方案:ATRA+ATO(维甲酸+三氧化二砷)方案:全反式维甲酸(ATRA)为25mg.m-2.d-1,分2-3次口服;三氧化二砷(ATO)0.16mg.kg-1.d-1,静滴,直至完全缓解。同时予以输血小板、营养支持及对症治疗。
2.2.4疗效
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 CR)[14]:同前。复发(Relapse)[15]:同前。
3、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5.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平均数±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表示,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p< 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研究结果
4.1一般特征
4.1.1患者特点
选取的形态学符合APL的PML/RARa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的20例患者(观察组)中位年龄42岁(18-73岁)。其中男性患者8例,女性患者12例,男女比例2:3。FAB分型:急性髓系白血病M3v型4例,急性髓系白血M2型11例,急性髓系白血病M4型4例,急性髓系白血病M5型1例。以急性髓系白血病M2型为主,占55%。选取的30例同期骨髓细胞形态学与分子生物学一致的非M3的AML患者(对照组)中位年龄为60岁(13-71岁),其中男性患者15例,女性患者15例,男女比例1:1。两组年龄及性别构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415、0.487)。FAB分型:急性髓系白血病M2型22例,急性髓系白血病M4 4例,急性髓系白血病M5 4例,其中M2型占73.3%。
 图4.1两组患者性别比较
图4.1两组患者性别比较
表4.1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比较
| 项目 观察组(n=20) 对照组(n=30) p |
| 性别0.487
男 8(40%) 15(50%) 女 12(60%) 15(50%) 年龄 43.60±14.5447.23±15.770.415 |
4.1.2临床表现
观察组与对照组均以出血(牙龈、皮肤出血、女性月经增多)、感染(发热、咳嗽、咳痰、乏力)等起病,而在以出血起病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在阳性体征如(胸骨压痛、肝脾肿大、淋巴结肿大)等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诱导缓解治疗过程中观察组与对照组并发感染、消化道症状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诱导缓解治疗中并发出血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4.2两组患者临床表现特点
| 临床表现 观察组 (n=20) 对照组(n=30) p值 |
| 起病特点(例,%)
出血 15(75.00) 6(5.00) 0.001 乏力15(75.00) 17(56.6) 0.186 感染10(50.00) 20(66.67) 0.239 阳性体征(例,%) 胸骨压痛 12(60.00) 20(66.67) 0.630 肝脏肿大 3(1.50) 5(16.67) 0.875 脾脏肿大 4(8.00) 4(13.33) 0.529 淋巴结肿大 3(1.50) 6(20.00) 0.652 诱导缓解治疗并发症(例,%) 出血14(70.00) 10(33.33) 0.011 感染10(50.00) 20(66.67) 0.239 消化道症状15(75.00) 15(50.00) 0.077 |
4.1.3实验室特征
4.1.3.1血常规、出凝血检查、LDH
观察组与对照组在凝血功能上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血小板计数、血红蛋白、白细胞、LDH等均无差异(p>0.05)(具体见下表3)。
表4.3两组患者实验室指标比较
| 实验室指标 | 观察组(n=20) | 对照组(n=30) | 统计量 | p值 |
| WBC(×109/L) | 14.10(1.08-200) | 7.2(0.64-101.06) | -1.307 | 0.191 |
| HGB(g/L) | 70.50(42-140) | 71.50(28-123) | -1.09 | 0.913 |
| PLT(×109/L) | 57.00(7-235) | 75(7-149) | -1.011 | 0.312 |
| LDH | 364.50(245-678) | 364(231-789) | -1.07 | 0.304 |
| 骨髓早幼粒细胞比例 | 81 (60.5-87.5) | 18.5 (13-23) | 35.294 | 0.0001 |
| PT延长≥3s(例,%) | 4.089 | 0.043 | ||
| 是 | 9 (45.00) | 22 (73.33) | ||
| 否 | 11 (55.00) | 8 (26.67) | ||
| APTT延长≥10s(例,%) | 4.434 | 0.035 | ||
| 是 | 8 (40.00) | 21 (70.00) | ||
| 否 | 12 (60.00) | 9 (30.00) | ||
| FIB≤1.5g/L(例,%) | 5.223 | 0.022 | ||
| 是 | 9 (45.00) | 7(23.33) | ||
| 否 | 11 (55.00) | 23(76.67) |
4.1.3.2 骨髓检查、流式免疫分型特点
所有观察组患者骨髓细胞化学染色均为POX染色强阳性,NES强阳性,但不被NaF抑制;骨髓早幼粒细胞百分比均值为81%见表4.3;在对照组患者中M2患者骨髓细胞化学染色均为POX染色强阳性,NES强阳性,但不被NaF抑制。M4骨髓细胞化学染色均为POX染色阳性,NES阳性,但不被NaF抑制,M5骨髓细胞化学染色均为POX染色阳性,NES强阳性,被NaF抑制。骨髓早幼粒细胞百分比均值为18.5%,两组患者的骨髓早幼粒细胞百分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流式免疫分型中,所有患者表达CD13+、CD33+、cMOP+、HLA-DR-,多数表达CD56+、CD117+、CD64+、CD34+。在对照组中所有患者均表达HLA-DR+、CD13、CD15+,部分表达CD117、CD64等。
4.1.3.2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
在观察组患者均进行染色体及分子生物学检查,其中10例为正常核型,10例存在染色体异常,染色体异常率50%;出现异常融合基因11例,其中PLZF-RARA阳性3例,其他基因异常8例,分别为:2例AML1-ETO基因,6例HOX11基因,出现基因异常占45%,11例未见异常融合的白血病基因。对照组中30例进行染色体及分子生物学检查,其中5例存在染色体异常,占16.67%,其余25例均为正常核型;出现基因异常8例,占26.67%,其中5例AML1-ETO基因阳性,MLL-ELL基因阳性2例,WT1基因阳性1例,其余22例均未见白血病融合基因。观察组与对照组在发生融合基因、染色体异常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012、0.029)。
4.2治疗与预后
4.2.1诱导缓解治疗疗效比较
观察组中14例对ATRA、ATO治疗无效,但经过常规化疗后14例达到完全缓解(CR),其中2例经ATRA联合小剂量化疗达CR,1例经,ATRA联合ATO 诱导治疗后达CR,3例无缓解,完全缓解率为70%,达CR中位时间为40.5(37-45)天;对照组中25例患者均经化疗后达CR,5例未缓解,CR率为83.3%,达CR中位时间为20.5(19-23)天;两组患者在CR率、达CR时间等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4.4。
表4.4两组患者治疗疗效指标比较
| 疗效指标 观察组(n=20)对照组(n=30)p值 |
| CR(例,%) 15 (75.00)29 (96.67)0.032
复发(例,%) 17 (87.00)15 (50.00)0.029 死亡(例,%) 9 (45.00)5 (16.67)0.043 达CR时间40.5 (37-45)20.5 (19-23)0.001 首次复发时间12(5-30)16.5(12-36) 0.010 |
4.2.2预后比较
随访截止时间2019年12月31日,在观察组中位随访时间23(5-72)月,无失访问患者。随访发现9例死亡,其中因脑出血死亡6例,复发后死亡3例,死亡率45%(9/20),复发17人,复发率87%,首次复发中位时间12(5-30)月。对照组中位随访时间36.5(15-72)月,无失访问患者,其中死亡6人,均为复发后死亡,死亡率5%(5/30),复发15人,复发率50%,首次复发中位时间16.5(12-36)月,二者在死亡率、复发率、首次复发时间上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4。
5讨论
FAB 协作组对AML的分型主要依据骨髓原幼细胞的形态、数量进行划分。APL在形态上有时易与 AML-M4、M5相混淆[16]。在本研究中,20例形态学符合APL的 PML/RARa 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中最终确诊急性髓系白血M2型11例,急性髓系白血病M4型4例,急性髓系白血病M5型1例,与既往报道相似。但APL细胞NES染色呈现强阳性,不被NaF抑制,骨髓流式细胞免疫分型提示存在CD13+、CD33+、c MOP+、CD34-、HLA-DR-,可供鉴别。2016年《WHO 造 血 及 淋巴组织肿瘤分类》将APL定义为t(15;17)伴PML/RARa融合基因阳性及其变异型的AML。约有5%的患者在细胞形态学上符合APL,但PML/RARa 融合基因是阴性。其中一部分患者诊断为PML/RARa变异型,对于这一部分患者的核型,既往报道的有t(11;17)(q23;q21)、t(11;17)(q13;q21)、t(5;17)(q23;q21),del(17q)、t(4;17)(q12;q21),即对应的 17 号染色体上 RARa 基因的伙伴基因为 PLZF、Nu MA、NPM、STAT5b、FIP1L1。另一部分患者则被诊断为不累及17号染色体的核型突变,如t(11;12)(p15;q13),突变基因为NUP98-HOXC13/11,inv(11)(p15;q22)等[17]。在APL靶向药物出现之前,多数APL患者在未达到CR前就死于颅内出血、DIC等并发症。ATRA、ATO 靶向药物出现后,因能诱导异常早幼粒细胞分化或凋亡,极大地提高了APL患者的缓解率和延长了生存期。但 PML/RARa基因阴性患者多对ATRA、ATO 不敏感,预后相对较差。为加强对此类患者的临床特点、治疗及预后的认识,我们将从以下几个发面进行讨论。
在本研究中,选取的20例观察组患者的中位年龄42岁(18-73岁)。其中男性患者8例,女性患者12例,男女比例2:3。选取的30例对照组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0岁(13-71岁),其中男性患者15例,女性患者15例,男女比例1:1。两组年龄及性别构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415、0.487)。这显示了形态学符合APL的PML/RARa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与急性非APL的急性髓系白血病在发病年龄及性别无差异。然而,既往研究表明[18],诊断非APL的AML患者的中位年龄应在65岁左右,男女性别比例为5:3,而在本研究中形态学符合APL的PML/RARa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中位年龄为42岁,男女比例2:3,考虑与样本量较少有关,以及其本身形态学与APL相似,因而具有一定的APL的流行病学特征。
在本研究中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早期出血(以出血起病、诱导化疗过程中出血)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观察组与对照组在凝血指标(PT、APTT、FIB)、血小板计数等方面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观察组中早期因脑出血死亡的患者有6例,以上均说明形态学符合APL的PML/RARa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具有早期出血倾向,这与2019年苏于泰等人[17]在研究形态学符合 APL 的 PML/RARa 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临床特征中的结果一致。考虑可能与APL早期出血机制一致,即细胞人类APL细胞系NB4细胞扰乱凝血功能有关。而观察组与对照组在以感染(发热、咳嗽、咳痰、乏力)起病等方面、阳性体征、诱导治疗过程出现其他并发症等均无差异(p>0.05)。因此,在诊断此类疾病时应注意出血的防范,尤其注意避免颅内出血的发生。
所有观察组患者骨髓象均提示早幼粒细胞高表达,平均值为77.3%,骨髓细胞比例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一结果与2019年苏于泰[17]研究形态学符合APL的PML/RARa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临床特征中报道的骨髓象结果相似。在骨髓细胞流式免疫分型中,所有观察组患者均表达CD13+、CD33+、cMOP+、HLA-DR-,多数表达CD56+、CD117+、CD64+、CD34+。如上所述APL患者骨髓流式细胞术免疫分型提示CD13+、CD33+、cMOP+、CD34-、HLA-DR-,而本研究中多数观察组患者仍表达CD56+、CD117+、CD64+、CD34+。CD56是存在于细胞表面的一种糖蛋白,能够介导细胞粘附和细胞毒性,然而其粘附分子的特性能使肿瘤细胞更具侵袭性,髓外浸润风险更高,最终导致预后差。2018年郑元海等人[19]研究AML免疫表型与预后的相关性也证实了此观点。CD34抗原是一种跨膜蛋白,主要表达于早期的造血前体细胞,其表达会随着前体细胞的分化成熟而逐渐减少。有研究显示[20-22]免疫分型中CD34+的AML患者较CD34-患者的完全缓解率低、整体生存期短,同时CD34+患者中难治性比例高。CD117是一种跨膜酪氨酸激酶受体,在正常骨髓干细胞中无表达,但在AML中表达增高,有研究显示[23]CD117的高表达与AML耐药密切相关,也曾有文献报道[24]CD117+的非APL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CR率低于CD117-的患者,但多数学者认为CD117与AML患者预后及疗效尚无明确定论。在本研究中,多数观察组患者仍表达CD56+、CD117+、CD64+、CD34+(80%),而对照组极少数CD117+,大多数不表达CD56、CD34,最终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在CR率、死亡率等方面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同时也证实CD34+、CD56+、CD117+的AML患者较CD34、CD56、CD117阴性预后较差。CD64是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分化的抗原,主要在单核巨噬细胞表达,因此主要见于M4及M5患者[19],在本研究中所有M4、M5患者均有CD64表达,与既往报道相符。
一般AML的治疗与预后危险分组息息相关,按照第九版内科学中AML常见的染色体与分子学异常的预后意义危险分组及Sanz预后分层标准,在本研究中观察组预后良好的AML患者有3例,中等预后10例,预后不良7例。20例患者均根据预后分组选择适当的化疗方案治疗后,15例患者达完全缓解,13例患者出现缓解后复发,9例患者死亡,20例患者完全缓解率、2年复发率、2年死亡率分别为75%、65%、45%,相比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预后较差(p<0.05)。虽然近年来AML患者在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的预后分层指导化疗和进步的支持治疗下,生存率大大提高,但生存率大大提高的主要是预后良好组的患者,而大部分的中等预后及不良预后的患者,缓解后治疗、复发及死亡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结局[25]。因此,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SCT)仍被认为是治愈中等预后及不良预后的患者的唯一有效手段。2018年Laura[26]等人通过对40例形态学支持APL而PML/RARa基因阴性的AML患者临床研究发现,在完全缓解后采用早期异基因移植可明显改善患者预后、减少复发率。同年黄晓兵等人[25]通过研究87例中等及不良预后的87例AML患者时发现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AML的有效方法,尤其是针对缓解后复发的患者。而在本研究中20例患者因为自身及经济原因未行allo-HSCT治疗,因此,笔者认为在以后的临床工作中,针对中等及不良预后的形态学符合APL的 PML/RARa 基因阴性的AML患者,在诱导化疗缓解后及化疗后复发时,可对此类患者可考虑异基因移植治疗,以期提高患者长期生存率、减少复发率。
细胞遗传学是预测AML预后的重要指标,大部分基因突变与核型异常与AML的预后密切相关,且大多数较基因、核型正常患者预后差[19]。在本研究中观察组较对照更易发生基因融合、染色体异常(p值分别为0.012、0.029),且在预后分析中,观察组较对照组具有更高死亡率、复发率(p值分别为0.029、0.043)也证实了这一点。下面我们将对观察组中各个异常基因及染色体进行分析:既往有研究表明AML中t(16,16)(p13.1,q22)、t(8,21)(q22;q22.1)伴有异常基因AML1-ETO预后良好,完全缓解率达90%以上,10年生存率达55%[27-28],在本研究中观察组2例AML患者存在t(16,16)(p13.1,q22),1例t(8,21)(q22;q22.1),对照组中1例存在t(8,21)(q22;q22.1),以上具有t(8,21)(q22;q22.1)伴有异常基因AML1-ETO的患者均达完全缓解,现已生存2年余,仍处于持续缓解状态,与既往报道相符,但观察组中1例t(16,16)(p13.1,q22)伴异常HOX11基因在诱导缓解治疗未结束时因颅内出血死亡,且实验组中另外5例患者无染色体异常伴HOX11异常基因也于诱导缓解未结束而发生颅内出血死亡。这考虑与既往报道[29-31]证实携带有HOX11的AML患者复发及死亡率极高、预后差相似。关于AML患者出现t(11,12(p15,q13),自1998年-2019年有大量的个案报道[32-33],它可出现于M1、M2、M3、M4、M5等亚型中,致病机制尚不明确,但多数患者不易缓解、早期死亡率高,且缓解后易复发。本研究中观察组3例t(11,12(p15,q13)患者诱导缓解后出现复发,与既往报道相似。在观察组中我们也发现3例患者具有i(17)(q10)异常,目前尚文献报道出现此类染色体异常患者预后如何,而在本研究中2例患者均发生缓解后复发。最后,在本研究观察组中我们也发现3例PLZF/RARα阳性患者,其染色体分别为[46,XY,t(5;17)(q35;q21)]、[46,XY,t(11;17)(q23;q21)]、(46,XY),其中1例早期因发生DIC死亡,其余两例均发生复发。这与2019年Wang等人[32]报道20例PLZF/RARα阳性的APL患者临床特征结论相似。
此外,关于形态学符合APL的 PML/RARa 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治疗,既往研究提示多数患者对ATO及ATRA不敏感甚至无效,应结合基因及染色体核型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在没有条件对ATRA、ATO敏感基因进行检测或者次两种药物疗效较差时应尽早采用急性髓系白血病常规化疗方案,以期提高患者完全缓解率、减少复发,改善预后[17,35-36]。在本研究中所有患者均进行PML-RARa基因检测,20例患者中5例无缓解,1例经ATRA联合ATO 诱导治疗后达CR,14例患者对ATRA、ATO治疗无效,但经过AML常规化疗后均达到完全缓解(CR),完全缓解率为75%,此治疗结果与既往报道相似。
另外,虽然临床上不乏出现骨髓形态学、骨髓细胞化学染色支持APL,甚至流式免疫分型也支持APL,但对其进行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检测后其不支持APL的诊断的患者。对于此类现象目前尚无学者对其进行详细、系统解释,于是作者通过查阅此类文献报道进行总结归纳如下:一方面主要考虑人为因素,即阅片者由于主观因素造成影响,但通过查阅文献后此类现象层出不穷,且血液科医师有过硬阅读骨髓片能力,因此人为因素仅仅是极少数情况。另一方面,既往有报道[17]认为主要是PML-RARA融合基因变异易位的APL,如上所述t(11;17)(q23;q21)、t(11;17)(q13;q21)、t(5;17)(q23;q21),del(17q)、t(4;17)(q12;q21),即对应的17号染色体上RARa基因的伙伴基因为 PLZF、Nu MA、NPM、STAT5b、FIP1L1。另一部分为不累及 17 号染色体的突变,如 t(11;12)(p15;q13),突变基因为NUP98-HOXC13/11,inv(11)(p15;q22)等。少数报道认为除了存在PML及RARA基因外,可能存在MYC、FNDB3D、MECOM基因使非M3的AML患者骨髓形态呈现APL样[36-37],以及与EZH2(Enhancer Of Zeste 2 Polycomb Repressive Complex 2 Subunit)基因功能改变有关[38]。因此,目前关于形态学符合APL的PML/RARa 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与APL患者的骨髓细胞形态学具有更细微差异及发生机制仍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我们研究表明形态学符合APL的 PML/RARa 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与APL患者具有同样的早期出血风险,应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出血。同时此类患者预后较差、复发率高,但对ATO及ATRA治疗不敏感,应更加全面地对基因及染色体的检测,尽早采用合适的急性性髓系白血病常规化疗方案,甚至进行allo-HSCT治疗,以期提高患者完全缓解率、减少复发,改善预后。
6、结论
(1)形态学符合APL的 PML/RARa 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具有较高早期出血风险;
(2)形态学符合APL的 PML/RARa 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预后较非APL的AML患者差;
(3)形态学符合APL的 PML/RARa 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对ATO及ATRA治疗不敏感,需尽早结合基因及染色体核型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必要时可行早期allo-HSCT治疗。
7、研究不足之处
本研究的人数有限,样本量来源单一,仅为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住院患者;由于条件限制,无法对形态学符合APL的 PML/RARa 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骨髓片与AML患者、APL患者的骨髓片进行进一步的对比研究。
参考文献
[1]Vaghani B D, Shah H R, Agrawal H, et al. Study of cytogenetic abnormalities in 190 cases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with its morphological and cytochemical correlation at a tertiary-care cancer institut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 and Public Health, 2015, 4(10): 1396-1401.
[2]Chattopadhyay A, Abecassis I, Redner R L. NPM-RAR binding to TRADD selectively inhibits caspase activation, while allowing activation of NFκB and JNK[J]. Leukemia & lymphoma, 2015, 56(12): 3401-3406.
[3] Kitamura K, Hoshi S, Koike M, et al.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but not arsenic trioxide differentiates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aemia cells with t (11; 17) in combination with all‐trans retinoic acid[J].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2000, 108(4): 696-702.
[4]Goto H, Kimura M, Hirano N, et al. NUP98-HOXC13 fusion gene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Pediatric case[J]. Pediatrics international: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Japan Pediatric Society, 2017, 59(10): 1105-1106.
[5]Xiang, Zhang, Xin, et al. MLL-rearrangement can resemble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Leukemia & lymphoma, 2019.
[6]Zhang X , Li F , Wang J , et al. RARγ-rearrangements resemble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and benefit from 3 + 7 regimen[J].
[7]Qin Y Z, Huang X J, Zhu H H. Identification of a novel CPSF6-RARG fusion transcript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resembling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Leukemia, 2018, 32(10): 2285-2287.
[8]Badar, Talha, Johnson, Laura, Trifilo, Katelyn,等. Detection of Novel t(12;17)(p12;p13) in Relapsed Refractory Acute Myeloid Leukemia by Anchored Multiplex PCR(AMP)-bas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J]. Applied Immunohistochemistry & Molecular Morphology Aimm, 2019, 27.
[9]Vaghani B D, Shah H R, Agrawal H, et al. Study of cytogenetic abnormalities in 190 cases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with its morphological and cytochemical correlation at a tertiary-care cancer institut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 and Public Health, 2015, 4(10): 1396-1401.
[10]张校辉,邢江涛,张玉娜,李建英,苗蕊,胡蕊,朱芸. 变异性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实验室检查结果分析[J]. 检验医学,2019,10:871-875.
[11]Gupta A , Reddy K G , Goyal M . “Faggot Neutrophils!” in Non-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A Rare Occurrence[J]. Indian Journal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Transfusion, 2018.
[112]Jie, Zhao, Jian-Wei, et al. The genetic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morphologically diagnosed as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Leukemia, 2018.
[13]Adams J , Nassiri M .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A Review and Discussion of Variant Translocations[J]. Archives of Pathology & Laboratory Medicine, 2015, 139(10):1308-1313.
[14]Cheson B D, Bennett J M, Kopecky K J, et al. Revise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for diagnosis, standardization of response criteria, treatment outcomes, and reporting standards for therapeutic trials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03, 21(24): 4642-4649.
[15]Thomas XThe management and treatment of acute leukemias in theelderly population. Expert Rev Hematol,2017; 10( 11) : 975 - 985.
[16]Arber, D. A, Orazi, A, Hasserjian, R,等. The 2016 revision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lassification of myeloid neoplasms and acute leukemia[J]. Blood, 127(20):2391-2405.
[17]苏于泰, 刘炜, 管玉洁,et al. 形态学符合APL的PML/RARa基因阴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临床观察[J]. 中国现代医药杂志, 2019(6):42-44.
[18]https://seer.cancer.gov/csr/1975_2014/browse_csr.phpsectionSEL=13&pageSEL=sect_13_table.13.html (Accessed on June 07, 2017).
[19]郑源海,林元峰,许瑞元,张志坚,文晓芳. 急性髓系白血病免疫表型特征与预后相关性分析[J]. 现代检验医学杂志,2018,04:90-94.
[20]Webber BA, Cushing MM, Li S.Prognosticsignificanceofflowcytometric immunophenotyping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J]. Int J Clin Exp Pathol.2008, l(2): 124-33.
[21]Mi YC, Bian SG, Xue YP, et al. Baixuebing [J]. 1997; 6(4): 194-198.
[22]Ahmad E I , Akl H K , Hashem M E , et al.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dult CD34+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Medical Oncology, 2012, 29(2):1119-1126.
[23]Mehnert JM, Kluger HM. Driver mutations in melanoma: lessons learned from bench-to-bedsidestudies [J]. Curr Oncol Rep. 2012 Oct;14(5):449-457.
[24]徐英英. 非APL急性髓系白血病抗原表达与临床疗效分析[D].延安大学,2019.
[25]Kristen Pettit, Richard A. Larson. Therapy-Related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M]//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2018.
[26]]黄晓兵,李成龙,王春森,祝彪,杨曦.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单中心临床疗效分析[J]. 重庆医学,2018,03:302-305.
[27]Grimwade D, Hills RK, Moorman AV, et al. Refinement of cytogenetic classification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determination of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rare recurring chromosomal abnormalities among 5876 younger adult patients trea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trials. Blood 2010; 116:354.
[28]Lutterbach B, Hou Y, Durst KL, Hiebert SW. The inv(16) encodes a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1 transcriptional corepressor.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999; 96:12822
[29]ia J, Pekowska A, Jaeger S, et al. Assessing the efficiency and significance of Methylated DNA Immunoprecipitation(MeDIP) assays in using in vitro methylated genomic DNA[J]. BMC Res Notes, 2010, 3: 240.
[30]Li ZG, Wu MY, Zhao W, et al. Detection of 29 types of fusion gene in leukemia by multiplex RT-PCR[J].Zhonghua Xue Ye Xue Za Zhi, 2003, 24(5): 256-8.
[31]阳洁,陈宏. 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HOX11基因的表达及意义[J]. 肿瘤防治研究,2015,05:478-480.
[32]宫本法,李其辉,李巍,等 . 伴 t(11,12)(p15,q13)急性髓系白血病二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J]. 中华血液学杂志,2013,34(10):830-833
[33]Hua J, Bao X, Xie Y. A Rare Morphology Resembling APL with t (11; 12)(p15; q13)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J]. Clinical laboratory, 2019, 65(10).
[34]Maximilian Stahl, Martin S. Tallman. Differentiation syndrome in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aemia[J].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2019.
[35]Zhang X , Li F , Wang J , et al. RARγ-rearrangements resemble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and benefit from 3 + 7 regimen[J].
[36]Poddighe, Pino J, Wessels, Hans, Merle, Pauline,等. Genomic amplification ofMYCas double minutes in a patient with APL-like leukemia[J]. Molecular Cytogenetics, 7(1):67.
[37]Wang H Y, McMahon C, Ali S M, et al. Novel FNDC3B and MECOM fusion and WT1 L378fs* 7 frameshift mutation in an acute myeloid leukaemia patient with cytomorphological and immunophenotypic features reminiscent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aemia[J].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2016, 172(6): 987-990.
[38]Coccaro N , Zagaria A , Orsini P , et al. RARA, and, RARG, Gene Downregulation Associated with, EZH2, Mutation in Acute Promyelocytic-Like Morphology Leukemia[J]. Human Pathology, 2018:S0046817718300753.
综述
亚砷酸致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肝损害的研究进展
摘要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亚砷酸的应用使其成为一种可治愈性疾病。然而在亚砷酸带来显著疗效的同时,其产生的不良反应也引起了临床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肝脏的毒副反应方面。本文就亚砷酸致诱导分化治疗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肝损害进行详细介绍。
关键词: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亚砷酸;肝功能损害
前言
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是一种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恶性克隆性疾病。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是AML中的一种特殊亚型,即英、法、美(France America British,FAB)分型中的M3型,其典型的特征就是约95%的APL患者具有特异的(15;17)染色体异位及 PML/RARa融合基因形成[1]。近年来,流行病学研究证实,APL在国外同期AML中占10%~15%[2],而国内报道的APL发病率占同期AML的3.3%~21.2%[3]。在临床上,APL主要以起病急、病程进展迅速以及严重的出血倾向为特点。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APL曾被认为是AML中恶性程度最高、致死率最高、预后最差、临床过程最凶险的类型,后随着全反式维甲酸(all-trans retinoic acid ,ATRA)、亚砷酸(arsenic trioxide,ATO)及蒽环类药物的应用后,使其达到接近90%的完全缓解率,80%的治愈率[4] ,成为目前AML中预后最好的类型。
ATO在治疗APL患者的初发和复发方面均具有显著疗效。自2004年开始,ATRA联合ATO治疗方案已逐渐成为APL的一线诱导分化治疗方案,可使初发的APL患者的CR率高达90%~95%,长期生存率达90%以上[5-7]。尽管如此,在ATO 的应用带来显著疗效的同时,其产生的不良反应也引起了临床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肝脏的毒副反应方面。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对ATO所致的肝脏毒性的特点进行总结和研究便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事实上,迄今为止,鲜有专门的临床研究探讨加用ATO是否会加重APL患者的肝脏毒性,以及研究肝脏毒性的特点。本文结合最新的研究报道,全面综述了ATO在诱导分化治疗APL过程中的肝脏毒性作用,详细介绍其发生机制及防治措施。以期为以后临床APL患者诱导分化治疗过程中肝损害的发生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提供有理有力的参考依据,以期改善APL患者诱导分化治疗期间的生活质量,保证诱导分化治疗的顺利完成。
1、APL发病机制:
典型的APL细胞遗传学特征表现为第15号和第17号染色体断裂并发生易位。即第15号染色体上的PML( pro-myelocyticleukemia) 基因和第17号染色体上的维甲酸受体α( retinoic acid receptor α,RARα) 基因融合,形成PML/RARα融合基因,编PML/RARα融合蛋白。而PML-RARα融合基因一方面通过抗RAR/RXR通路阻断分化,另一方面使PML脱离其正常定位,抑制其抑制细胞增殖及促细胞凋亡的功能,故PML-RARα融合基因对PML和RARα均有负性抑制作用,使血细胞异常增殖、粒细胞分化停滞在早幼粒细胞阶段,阻碍细胞的进一步分化从而导致异常早幼粒细胞增多,最终导致APL的发生。PML/RARα融合基因已成为经典的APL致病基因,其致APL的发生机制已基本被阐明,这也为ATRA及ATO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2、ATO在APL中作用机制:
亚砷酸又名三氧化二砷(ATO),是一种原浆毒性物质,也是有毒物质砒霜的主要成分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ATO就被我国哈尔滨医科大学张亭栋教授应用于APL的治疗,并且取得较好疗效,随后上海瑞金医院的陈竺、陈赛娟院士团队及其他国内外学者对其治疗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主要通过降解PML/RARa融合蛋白的PML部分来快速降解PML/RARα融合蛋白,最终诱导白血病细胞分化、凋亡、自噬、靶向白血病干细胞等发挥疗效,同时体外研究实验也发现ATO存在剂量依赖双重活性,低浓度( 0.1~0.5μmol / L) 时诱导白血病细胞分化,高浓度(0.5~2.0μmol / L) 时引发细胞凋亡,但对造血干细胞无毒性作用。药代动力学研究表明其在人体内血药浓度分布较广,兼具诱导凋亡与诱导分化作用[8]。然而,其不仅作用于白血病细胞,也作用于全身其他脏器,均可引起一系列毒副反应。
3、ATO治疗APL的不良反应:
ATO治疗APL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疗效,是我国医务工作者对世界医学界的重大贡献之一。但同时,ATO治疗APL的毒副反应仍应引起人们的重视。常见的毒副作用有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分化综合征(Differentiation syndrome ,DS)、肝功能损害、皮肤病变等,较少见的有心脏毒性、胃肠道反应、神经系统毒性、造血系统及男性生殖系统的毒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等。
3、1 DIC:
APL通常不是一种快速增殖性急性白血病,且尚不清楚APL的临床前期通常有多久,但得到诊断时骨髓往往已几乎全被恶性早幼粒细胞代替,从而导致严重贫血、血小板减少和中性粒细胞减少、凝血功能障碍、DIC等。DIC主要表现为:频繁而严重的出血(皮肤、粘膜、牙龈出血、颅内出血、女性月经增多等)、凝血功能障碍(PT、APTT延长、低血浆纤维蛋白原、血浆D-2聚体升高)、其他各脏器功能障碍等。属于医疗急症,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其可引起多达40%的患者出现肺或脑出血,最终死亡发生率达10%-20%[9]。尚不完全清楚DIC发生的机制。但有研究表明组织因子及膜联蛋白Ⅱ对DIC的发生有主要的影响[10-11]:目前DIC暂无较好的治疗方案,但可以进行预防,有研究表明白细胞计数、幼稚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纤维蛋白原、PT、APTT、肌酐、体重指数等均对早期DIC预测有一定作用。
3、2分化综合征(DS):
又称维甲酸综合征,是一种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有时称为“细胞因子风暴”。主要表现为呼吸困难(发生率59%-95%)、不明原因发热(发生率53%-74%)、体重增加>5公斤、肌肉骨骼肌疼痛、不明原因低血压(发生率12%-39%)、急性肾功能衰竭和胸部X线片显示肺内浸润、胸腔积液或胸膜或心包积液(发生率53%-81%)[12]等,罕见症状包括急性弥漫性肺泡出血和急性发热性皮肤病(sweet syndrome)。流行病学证据表明25%的DS由ATRA和(或)ATO诱导分化治疗APL时所致。据文献报道单用ATRA治疗APL患者,DS发生率为2%-31%,然而单独使用ATO治疗APL患者,DS发生率为7%-60%,最终双诱导治疗APL患者DS发生率为14%-25%,这表明ATO与ATRA联合应用并不增加APL患者DS的发生率[13]。此外,也可发生在使用上述药物的复发或难治性APL患者中。迄今为止,对于接受ATRA或ATO治疗后的患者,哪些更有可能发生或不太可能发生DS,没有可靠的预测因素。但曾有报道显示诊断时白细胞数升高、白细胞增长迅速、APL原始细胞表达CD13或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升高的患者中DS发生率增加,但随后的研究证实BMI升高仅是发生DS的危险因素[14]。关于发生机制目前尚不清楚,多数报道认为是可能与IL-1β、IL-8、 CCL2 、CD11b、CXCL8和 G-CSF分泌增多有关[15-16]。
3.3肝功能损害:
ATO在诱导治疗期间导致肝功能损害已被临床工作者广泛观察到,2008年刁习君等人[17]研究发现有32%出现丙氨酸转氨酶升高,而邓春晓等人在研究ATO肝损害时,发现在38例患者中只有5例发生肝功能损害[18]。2010年印度的一项研究[19]详细分析了ATO所致的肝损害,其中有33%的患者发生了肝损害,7%的患者发生3/4级肝损害需要停用ATO。2013年HAO等人[20]研究表明应用ATO治疗APL以及晚期肝癌的病人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肝功能损伤,抑制肝脏功能的修复,影响患者预后,甚至在一些回顾性研究表明持久饮用被三氧化二砷污染的水与肝细胞肝癌的发生密切相关。2013年张珏等人[21]通过研究三氧化二砷对小鼠肝脏祖细胞的实验研究表明,ATO能影响肝脏祖细胞的增值,最终导致肝损害。另外,有文献报道,单用ATRA治疗APL时出现肝功能异常的比例12%-30%[22];单用ATO治疗APL时其发生率为 63.6%[23];维甲酸联合亚砷酸治疗APL时肝功能损害者占65.6%,这与单用维甲酸或亚砷酸无统计学差异。多数研究提示ATO所致肝功能损害为I-II级,主要表现为肝酶和或胆红素轻度升高,无肝区疼痛、黄疸等报道,化疗用药均无需中断。而III-IV级肝功能损害较为少见,但仍有文献报道其发生率高达10%[24],一旦出现III-IV肝功能损害则应停用ATO,进行保肝治疗,待肝功能恢复至III级以下,继续使用ATO,后长期随访患者肝功能后发现其均可恢复正常。目前ATO致肝功能衰竭仍较为罕见。
3.4 ATO常见副作用还有Q-T间期延长、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肾脏毒性、皮疹、皮肤干燥、手足麻木等。
4、ATO并发肝损害
据WHO统计,药物引起的肝损伤已经上升为全球肝病死亡原因的第五位,发生率为1.4%-8.1%,而抗肿瘤药物引起的肝损伤占药物性肝损伤的1/5-1/4,成为药物性肝损害第二大病因[25]。在X,药物是引起急性肝衰竭的主要原因。药物性肝损伤占非病毒性肝病的20%~50%,占暴发性肝衰竭的 15%~30%[26]。对于APL患者,在诱导分化治疗过程中,常见的化疗药物如ATRA、ATO、蒽环类等均具有一定的肝脏毒性,容易引起肝脏损伤,导致化疗药物减量、延迟用药甚至停药等,影响了患者的治疗及生活质量。因此明确ATO诱导分化治疗期间肝损害情况尤为重要,以下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来阐述ATO诱导分化治疗引起的肝损害。
4.1ATO在体内的代谢
ATO进入体内后易被红细胞摄取,在进入体内30-60分钟时,血清ATO浓度可达峰值,并随后快速分布至其他组织。据研究报道ATO最初分布于肝脏、肾脏、肌肉和皮肤,最终分布在所有组织中(包括脑)[27]。而一般肝脏对潜在的有毒物质代谢主要涉及两个时相[27],而ATO在肝脏代谢亦是如此。第一时相,药物存在于肝脏滑面内质网中,经肝微粒体混合功能氧化酶系统的作用发生氧化、还原、水解等反应,增加其水溶性。其中细胞色素氧化酶(cytochrome oxidase, CCO)是参与反应的主要酶,且与大部分内源性、外源性有害物质代谢有关。第二时相,主要是第一时相的产物在肝细胞胞浆通过催化酶的作用与极性配体(谷胱甘肽、葡萄糖醛酸、硫酸盐、氨基酸等)结合,通过结合作用不仅掩盖了药物分子的某些功能基因,而且可以改变其理化特性,形成低毒、水溶性高的代谢物,经尿液、胆汁排出体外。而关于砷剂的排泄,一项研究[28-29]分析了人类接受一种静脉用砷放射性同位素后的情况,发现砷剂的清除经历3个阶段:第1阶段:清除非常迅速,即在ATO进入体内后的最初2-3个小时,超过90%的砷经重新分布和肾脏排泄而从血液中被清除;第2阶段:砷进入体内后的3小时-7日;第3阶段:砷进入体内后的8日或更长时间。
4.3 ATO导致肝损伤的发生机制
在大多数情况下,药物经过肝脏代谢后,成为低毒物质排出体外。但有些药物在经过CCO酶系作用下,可转化为自由基、亲电子基或活性氧等有毒有害物质,导致肝脏损害[26-27]。另外,当参与反应的酶被抑制或不足时,将导致药物或其代谢产物在体内的大量蓄积,从而影响药物、代谢物的生物转化,最终直接导致肝脏损害。
目前关于亚砷酸致肝损害的机制尚不清楚,但其可能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点:( 1) ATO的原浆毒性作用: 肝细胞线粒体是ATO最敏感的细胞器,ATO进入体内可导致其被破坏。而线粒体的结构、功能改变与细胞凋亡的发生息息相关。最新研究认为ATO可显著性抑制肝脏线粒体细胞色素C氧化酶及ATP酶的活性。当这2种酶的活性受到抑制时,必然引起氧化磷酸化过程受阻,致酶自线粒体和细胞内渗出到血液中增强其活性[30],最终导致肝损害。( 2) ATO可抑制细胞生长作用:ATO通过阻断或延缓细胞DNA合成和有丝分裂时相,使细胞停滞在细胞分裂的S期和 G / M 期,从而抑制细胞生长。另外,研究发现,ATO对细胞增殖呈双向性,即在低浓度下可促进细胞增殖[31],而在高浓度下则抑制细胞的增殖,而这种双向作用可能与细胞生长因子有关。( 3) ATO具有过氧化作用: 氧自由基可触发细胞膜上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过氧化链式反应,使内质网、溶酶体、线粒体等生物膜结构破坏,可使DNA变性、蛋白质氧化、脂质过氧化,导致细胞的一系列功能紊乱,最终使细胞发生凋亡。(4)ATO诱导细胞内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产生、抗氧化能力降低,致使细胞的氧化和抗氧化平衡遭到破坏,导致细胞氧化损伤的发生,最终使细胞生存率降低[32],导致肝损害的发生。
此外,在少数特异质个体中,小分子的药物经过细胞色素P450作用后的代谢产物可以与肝内某些特异性蛋白结合形成抗原,诱导免疫应答,导致肝脏的免疫病理损伤[28]。
5、肝损害的预防及治疗
抗肿瘤药物因具有较低的靶点选择性,且大部分药物都会在肝脏进行代谢,因此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也会对人体正常肝组织细胞也具有一定的杀伤作用,从而造成肝损伤。为了将诱导分化治疗过程中ATO对肝脏的损伤程度降到最低,及时加用适当的保肝药物尤为重要,下面主要介绍几类临床上常见的几种能改善肝功能的药物。
5.1甘草酸类
代表药物主要是异甘草酸镁,其作用机制为:(1)通过抑制磷脂酶A2的活性起到抗炎作用来保护细胞膜。(2)主要成分为甘草次酸,其化学结构与肾上腺皮质激素类似,因此具有类固醇样作用,包括抗炎、抗过敏及免疫调节作用。(3)免疫调节作用,可通过活化NK 细胞、诱发γ-IFN 等发挥作用。此外,有文献报道[33]复方甘草酸苷还有预防肝纤维化作用。多项研究表明异甘草酸镁对肝细胞增殖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对肝损伤具有良好治疗作用,还能够改善调节性T细胞的免疫的免疫调节功能,尤其是HBV携带者联合使用异甘草酸镁及拉米夫定有助于抑制化疗导致的HBV再激活,减轻化疗所致肝功能损伤程度。
5.2抗氧化类
代表药物主要是水飞蓟宾类和双环醇类,在临床上均可快速降低ALT、AST,尤其是ALT,护肝疗效显著。而目前临床上,水飞蓟宾主要是通过抗氧化和直接抑制各种细胞因子对肝星状细胞的激活达到抗纤维化的作用。双环醇则可显著抑制四氯化碳的活性产物氯甲基自由基与肝微粒体蛋白质和脂质的共价结合,有效清除自由基,同时也能改善肝组织炎症。
5.3 缓解胆汁淤积类
代表药物是腺苷蛋氨酸。腺苷蛋氨酸参与各种酶促转甲基和转巯基反应,能增加生成细胞内的主要解毒剂谷胱甘肽和半氨酸,增加肝细胞的解毒作用和对自由基的保护作用,可通过巯基反应促使胆汁酸经硫酸化的途径,改善胆汁酸代谢系统的解毒功能,防止或减轻毒物和胆汁酸的氧自由基损伤肝细胞[34]。此外,腺苷蛋氨酸能调控肝细胞的生长,还调控肝细胞的凋亡应答,并能抗炎和抗纤维化,保护肝细胞。
5.4保肝解毒类
代表药物为N-乙酰半胱氨酸(N-acetylcysteine NAC)、还原型谷胱甘肽(Glutathione GSH)及硫普罗宁等。NAC及GSH可通过清除各种活性自由基起到肝细胞保护功能,其中NAC能够转变为半胱氨酸进而转变为谷胱甘肽,增加了谷胱甘肽的合成和利用率,发挥抗氧化作用;其次能够替代谷胱甘肽而发挥解毒作用;最后其作为硫酸化作用的底物,可通过增加非毒性代谢的效率[35]从而保护肝细胞。然则还原型谷胱甘作为外源性还原剂,可补充机体发生氧化应激时消耗的还原性物质,增加体内GSH含量,提高机体抗氧化的能力保护肝细胞。而硫普罗宁,是一种含活性巯基的甘氨酸衍生物,既能通过降低线粒体ATP酶活性提高肝细胞内ATP含量,又可抑制肝细胞线粒体脂质过氧化,保护线粒体某些特异巯基功能,增加线粒体膜小分子多肽,改善肝细胞结构和功能。同时,也可恢复并维持肝脏线粒体谷胱甘肽含量,保护肝细胞。
5.5 肝细胞膜修复保护类
代表药物为多烯磷脂酰胆碱,其是构成细胞膜、亚细胞膜的一种磷脂。可通过与肝细胞膜及细胞器结合从而增强细胞膜的完整性、稳定性及流动性。还能通过降低炎症反应、减少氧化应激、脂质过氧化、抑制细胞凋亡保护肝细胞[36]。
在APL患者中,较严重的肝功能异常会迫使医师对化疗强度及疗程进行改变,因此对ATO诱导分化治疗导致的肝损害的防治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何时应用何种剂量的改善肝功能的药物,到目前为止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一些学者认为保肝药物的非必要使用可能会消减ATO的疗效。如Kann等[37]进行的细胞实验结果发现,调节谷胱甘肽的水平可以改变细胞对ATO诱导的细胞凋亡的敏感性。Akao 等人[38]在NB4(APL细胞株) 细胞中证实,当细胞内的GSH水平>40 mmol / L时,ATO不能诱导NB4的凋亡,而谷胱甘肽合成抑制剂可以完全恢复NB4对ATO的敏感性。血液病患者药物性肝损伤的预防和规范化治疗专家共识也曾指出,外源性谷胱甘肽治疗肝病的疗效仍值得商榷; 谷胱甘肽本身对肝细胞再生具有抑制作用[39]。而Akao Y等人[40]通过细胞实验证实GSH制剂可能是ATO用于治疗APL致肝损害的的最好指示剂。
在APL治疗的研究领域中,任何一个指南( 包括X国立综合癌症网络指南) 和专家共识都不曾把保肝药物的应用列为必需,也就说明保肝药物的应用尚存在争议,至少还存在确切的证据支持或反对保肝药物的应用,因此在临床APL的治疗中,应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并结合具体治疗药物和方案来使保肝药物的应用或不用有理有据,使药物的使用效果达到最佳。
参考文献
[1]Elsayed G M, Nassar H R, Zaher A, et al. Prognostic value of IDH1 mutations identified with PCR-RFLP assay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patients[J]. Journal of the Egyptian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2014, 26(1): 43-49.
[2]Borrow J, Goddard A D, Gibbons B, et al. Diagnosis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aemia by RT‐PCR: detection of PML‐RARA and RARA‐PML fusion transcripts[J].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1992, 82(3): 529-540.
[3]Chillón M C, González M, García‐Sanz R, et al. Two new 3′ PML Breakpoints in t (15; 17)(q22; q21)‐positive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Genes, Chromosomes and Cancer, 2000, 27(1): 35-43.
[4]Coombs C C, Tavakkoli M, Tallman M S.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where did we start, where are we now, and the future[J]. Blood cancer journal, 2015, 5(4): e304.
[5]Burnett, Alan K., et al. “Arsenic trioxide and all-trans retinoic acid treatment for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aemia in all risk groups (AML17): results of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The lancet oncology16.13 (2015): 1295-1305.
[6] MA H, YANG J. Insights into the All-trans-Retinoic Acid and Arsenic Trioxide Combination Treatment for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A Meta-Analysis[J]. Acta Haematol, 2015,134(2):101-108.
[7] Ghavamzadeh, Ardeshir, et al. “Comparison of induction therapy in non-high risk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with arsenic trioxid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ATRA.” Leukemia research66 (2018): 85-88.
[8]Pan X Y, Chen G Q, Cai L, et al. Anion exchanger 2 mediates the action of arsenic trioxide[J].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2006, 134(5): 491-499.
[9]Warrell RP Jr, de Thé H, Wang ZY, Degos L.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N Engl J Med 1993; 329:177.
[10]Mantha S, Tallman M S, Soff G A. What’s new in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coagulopathy in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Current opinion in hematology, 2016, 23(2): 121-126.
[11]Tiziano Barbui, Guido Finazzi, Anna Falanga. The Impact of All-trans-Retinoic Acid on the Coagulopathy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Blood, 1998, 91(9):3093-3102.
[12]Montesinos P, Bergua JM, Vellenga E, et al. Differentiation syndrom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treated with all-trans retinoic acid and anthracycline chemotherapy: characteristics, outcome, and prognostic factors. Blood 2009; 113:775.
[13]Lo-Coco F, Avvisati G, Vignetti M, et al. Retinoic acid and arsenic trioxide for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3, 369(2): 111-121.
[14]Breccia M, Mazzarella L, Bagnardi V, et al. Increased BMI correlates with higher risk of disease relapse and differentiation syndrom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treated with the AIDA protocols. Blood 2012; 119:
[15Tsai W H, Hsu H C, Lin C C, et al. Role of interleukin-8 and growth-regulated oncogene-α in the chemotactic migration of all-trans retinoic acid-treated promyelocytic leukemic cells toward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J].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07, 35(3): 879-885.
[16] Tsai W H, Shih C H, Lin C C, et al. 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 in the migration of differentiated leukaemic cells toward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J]. 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 2008, 31(5): 957-962.
[17]张茗文, 杨明丽, 周晋. 亚砷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不良反应及防治[J]. 临床药物治疗杂志, 2013, 11(2): 52-55.
[18]徐双年, 陈洁平, 刘建平, 等. 三氧化二砷联合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疗效的系统综述和 meta 分析[J].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2009, 7(11): 1023-1034.
[19]Mathews V, George B, Chendamarai E, et al. Single-agent arsenic trioxide in the treatment of newly diagnosed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long-term follow-up data[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10, 28(24): 3866-3871.
[20]Hao L, Zhao J, Wang X, et al. Hepatotoxicity from arsenic trioxide for pediatric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J]. Journal of pediatric hematology/oncology, 2013, 35(2): e67-e70.
[21]张钰. 三氧化二砷对小鼠肝脏祖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D].复旦大学,2013.
[22]Tsai W H, Shih C H, Lin C C, et al. 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1 in the migration of differentiated leukaemic cells toward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J]. 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 2008, 31(5): 957-962.
[23]Huang W, Sun G L, Li X S, et al.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clinical relevance of two major PML-RAR alpha isoforms and detection of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byretrotranscriptas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o predict relapse[J]. Blood, 1993, 82(4): 1264-1269.
[24]Mathews V, Desire S, George B, et al. Hepatotoxicity profile of single agent arsenic trioxide in the treatment of newly diagnosed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its impact on clinical outcome and the effect of genetic polymorphisms on the incidence of hepatotoxicity[J]. Leukemia, 2006, 20(5): 881.
[25]Niu C, Yan H, Yu T, et al. Studies on treatment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with arsenic trioxide: remission induction, follow-up, and molecular monitoring in 11 newly diagnosed and 47 relapsed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patients[J]. Blood, 1999, 94(10): 3315-3324.
[26]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 肿瘤药物相关性肝损伤防治专家共识(2014)简介[J]. 中华医学信息导报, 2014, 29(23):14-14.
[27] 沈洪,张蓓. 急性肝损伤研究进展[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9,18:2211-2213.
[28]Hoffman R S, Howland M, A LN N L S. Goldfrank’s Toxicologic Emergencies, 10th edn New York[J]. 2015.
[29]Schaumburg H H. Human neurotoxic disease[J].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neurotoxicology, 2000, 2: 55-82.
[30]高艳芳, 郭有, 苏林梁, 等. 低砷染毒致小鼠肝脏氧化损伤的影响[J]. 毒理学杂志, 2010, 24(2): 133-135.
[31]申旭波, 周远忠, 姜慧, 等. 亚砷酸钠对人肝细胞增殖的影响[J]. 遵义医学院学报, 2009, 32(1): 26-27.
[32]罗鹏, 王赟, 张爱华, 等. 亚砷酸钠对 L-02 肝细胞的氧化损伤作用[D]. , 2010.
[33]肖蓉. 异甘草酸镁联合拉米夫定防治HBsAg阳性的恶性血液病患者化疗后肝功能损伤的临床研究[J]. 现代预防医学,2011,24:5147-5148+5153.
[31]高旭东, 樊艳华. 中草药所致肝损伤[J].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09, 17(6):478-480..
[32] Bonilla E, Medina-Leendertz S, Villalobos V, et al. Paraquat-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in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effects of melatonin, glutathione, serotonin, minocycline, lipoic acid and ascorbic acid[J]. Neurochemical research, 2006, 31(12): 1425-1432.
[34]刘梅, 陆伦根, 曾民德. 多烯磷脂酰胆碱对肝细胞保护机制的研究进展[J]. 肝脏, 2006, 11(1): 43-45.
[35]Kann S, Estes C, Reichard J F, et al. Butylhydroquinone protects cells genetically deficient in glutathione biosynthesis from arsenite-induced apoptosis without significantly changing their prooxidant status[J]. Toxicological sciences, 2005, 87(2): 365-384.
[36]Akao Y, Yamada H, Nakagawa Y. Arsenic-induced apoptosis in malignant cells in vitro[J]. Leukemia & lymphoma, 2000, 37(1-2): 53-63.
[37]陈芳源, 达万明, 李冠军, 等. “血液病患者药物性肝损伤的预防和规范化治疗” 会议纪要[J]. 内科理论与实践, 2009, 4(5): 441-442.
[38]Akao Y, Nakagawa Y, Akiyama K. Arsenic trioxide induces apoptosis in neuroblastoma cell lines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caspase 3 in vitro[J]. FEBS letters, 1999, 455(1-2): 59-62.
致谢
三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活转瞬即逝,值此毕业论文完成之际,由衷感谢所有关心、帮助和支持过我的老师、同学和家人。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导师三年来对我的谆谆教诲和悉心关怀。三年来,导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风,深深的影响着我,为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使我受益终生。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从论文的选题、研究方向、资料收集、到后期的多次修改,老师给予我耐心的指导和支持,督促和帮助我完成了论文的撰写。在此向尊敬的老师致以深深的感激和谢意。
其次,我要感谢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尤其是我的每一位带教老师。在三年轮转学习过程中,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临床经验,不仅培养了临床思维、锻炼了动手能力,还对医学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热爱。
再次,我要感谢三年中一起轮转和学习的同学及朋友们,在我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给予我支持和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家人对我的支持和理解,正是有了家人的鼓励和支持,我才能顺利完成学业。
衷心感谢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评阅本论文的所有专家老师们。
1、如文档侵犯商业秘密、侵犯著作权、侵犯人身权等,请点击“文章版权申述”(推荐),也可以打举报电话:18735597641(电话支持时间:9:00-18:30)。
2、网站文档一经付费(服务费),不意味着购买了该文档的版权,仅供个人/单位学习、研究之用,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未经授权,严禁复制、发行、汇编、翻译或者网络传播等,侵权必究。
3、本站所有内容均由合作方或网友投稿,本站不对文档的完整性、权威性及其观点立场正确性做任何保证或承诺!文档内容仅供研究参考,付费前请自行鉴别。如您付费,意味着您自己接受本站规则且自行承担风险,本站不退款、不进行额外附加服务。
原创文章,作者:1158,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447766.cn/chachong/137521.html,